重启“诗”的此在之思 《谭诗录:实然非实然之间》的面向和面相
发稿时间:2020-06-22 11:52:00 来源: 华西都市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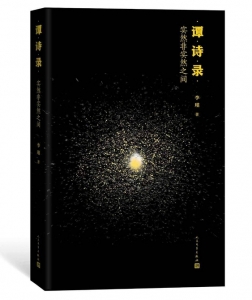
《谭诗录》
|编者按|
《谭诗录》是青年作家李瑾新近创作的一部诗论集,人民文学出版社2020年6月出版。
内容包括50篇谈论诗歌本体存在问题的短章,涉及诗歌和哲学、乌托邦、世俗化、虚无、死亡、身体、山水、民族主义、启蒙、自我等50个核心词汇之间的关系。不同于我们常见的从诗歌审美技巧、中西诗歌传统、诗歌发展历史与思潮等角度历史的、学理性的讨论诗歌,李瑾将诗歌抽象为一种情感和即时的思维,并以此为基点去接触诗歌的内心,探讨诗歌的本质,对诗歌进行解构和建构。
作品中谈论问题的切实,思想的深刻,内容的丰富,运思的独到,文风的特别,使这部作品不同于一般诗艺研究之作,具有独特的阅读价值。我们邀请首都经贸大学副教授、博士安歌与作者李瑾对话,谈“诗”论“思”。
诗之愉悦只有“在思维者”才可觉收
安歌:虽然我认为《谭诗录》是一部颠覆性的作品,但我拿到初稿时很怀疑你的写作目的。要知道,目下“生存的紧迫性”冲击力非常强大,当日常生活面临自由及责任断裂的危机,每个人陷入不安、怀疑甚至恐慌时,奢谈“诗”,且将“诗”界定为“即时的思维和情感,一旦创作完成,就不再是‘诗’”,会不会陷入布迪厄所讲的主观想象的危险境地?
李瑾:恰恰相反,我觉得现时恰恰是重张“诗”的逻辑之思的最佳时机。某一段时间,你有没有发现这样一种社会想象,自由也好,园丁式服务也罢,都没有缓解人的生存压力,也就是说,无论东西方这对文化“冤家”之间的沟壑多么宽大,立场多么不一致,面对“生存的紧迫性”都不知所措,值得注意的一个悖论是,人们追求的所谓“自由”恰恰会加重自己的负担——这是自负造成的,还是致命的误会,一时难以辨析清楚。但有一点是肯定的,“诗”代表了个体的原初经验,且与处境息息相关。谈论“诗”,就是谈论人,“诗”即是人唯一的终身/终生问题。也就是说,假如“人只剩下了活着这一事实本身”,谈论“诗”,自然便是“活着”这一问题。
安歌:这么说来,你将“诗”交给哲学了。问题是“诗”已经很成熟了,荷尔德林便说写诗是“人的一切活动中最为纯真的”,现在,你将谈论“诗”和“活着”相互印证,是不是会引起错觉,即我们以往在说“诗”这个词汇时,并没有搞清楚什么是“诗”?
李瑾:我觉得可以这么说。自始至终,“诗”始终没有一个清晰的概念——倒是有一个明白的(分行)形式,我们在使用“诗”这个词汇时,往往相当然地认为“诗”的所有问题都已解决,只要说、只要写就可以了,如此一来,关于“诗”的本质问题被等同于工具问题。事实上,“诗”和“人”一样,都没有被讨论清楚,而越迷糊,才越会表现出崇高的和超越性价值。我个人的感觉是,之所以我们没有全然掌握“诗”的“源”、“然”问题,在于我们被“文字”包围了,没有看到自己“是”的样子。如此一来,即便身为“诗”工,也无法摆脱萨特口中的“自欺”状态。
安歌:但“诗”总是“物质”性的,需要呈现,需要被阅读/感知。
李瑾:在《谭诗录》中,我已经说了,“诗”作为内在个我或知性的图式化,其实际过程既难以发现,也难以展现,我们察觉到的只是知觉,一种被视觉、听觉转译了的情感。同时,我还认为,“诗”自沉思开始,至沉思结束,其中的愉悦只有“在思维者”或者说诗人才可以觉收,外人无从知晓:我们获知的只是语言、文字和由其构建起来的精致的“感觉”,无论从“诗”中获得了多么大的精神享受,我们都落后了——“诗”不是知识和真理(这些都是过去式),而是“将来的状态”。而且。我还认为,对作者特别是他的内在个我而言,他者进入的完全是一个不同的心域。这里,并不是否定对“诗”的认知或欣赏,而是说对问题的洞识不能取代思维。通俗地说,假如说“诗”是一种本能,认知或欣赏是一种能力,两者之间的差别犹如天壤云泥。
“人”比“诗人”更有诗性和诗意
安歌:这么说来,“诗”是不可以理解的了?
李瑾:不是的。我的意思是说,“诗”的存在和显现并非同时发生的。内在个我感受到“诗”的存在时,他人尚一无所知。尽管“诗”和哲学同一源头,但“诗”的存在和显现与哲学的完全不同,因为哲学的需要一个他者作为先决条件,但“诗”作为沉思性思维,是完全内在的,不需要一个显性的接受者——请注意,我一直使用“转译”这个词汇涵定读者,“诗”不是纯粹的主体,纯粹的主体需要客体的存在,由此保证主体的客观实在性。“诗”和人/哲学不一样,“诗”存在于世界,但不属于世界,它只能感知,不能被感知,也就是不依赖于读者更不会主动去服务。一个诗性的个体眼中的世界,是一个自我表现支配的世界。“诗”消失,意味着某种思维的湮灭,纯粹的生物性个我世界的显现,是客观的,而非实在的。因此,我的结论是,对“诗”的理解——其实是一种自以为是的理解——完全出于错觉,“诗”的显现本身就是假象,而我们则试图给出一个合情合理的对应。
安歌:这就赋予一种“诗”的普遍性规定:人人都是诗人,无论他是否从事“诗”这一行当。
李瑾:是的,我是这么认为的。我甚至还认为,“人”比“诗人”更有诗性和诗意。“诗人”已被某种价值和语境规训,焦虑未来,故而粉饰现在,而“人”则在或者还在他的本然状态,故而更能敞开无意识的世界。补充一点,对“诗”的这种理解,可以在博纳富瓦那里得到呼应。这位法国诗人即不守陈规陋矩作诗,他不在意“一致性”“规范化”,而是看重转瞬即逝的“现时存在”及诗人即时即刻的内心感受。
写作时抱定唯一主义“人”即“诗”
安歌:说到博纳富瓦,我忽然意识到一个问题。你的《谭诗录》中体现诗学/文艺思想的主体部分居然没有引语,没有涉及到一个诗人或学者的名字,而现在你甚至谈到了萨特。你是有意回避吗?
李瑾:《谭诗录》主体部分,共有五十个切入点,分别探讨了“诗”和个人、不安、哲学、乌托邦、世俗化、思维、价值、暴力、知识分子、空间、时间、自媒体、语词、批评、翻译、极端、虚无、民族主义、视觉、心、气、道、中、局限、阅读、启蒙、男女之欲、真理、故乡、音乐、形而上之自杀、身体、审美、意识形态、作为一种非实然的国家、历史、自然权利、异化、象、山水、先锋、叙事、意象、意境、偏转、结构、自我、理智、虚之间构的关系——这些都是“诗”不可或缺的面向甚至涉及真相。在谈论这些问题时,我用的都是自己的话语——当然,前提是大量融合了我认同的前贤时士的观点。之所以并有索引、注解并点名道姓,是怕我自己的理解被贴上“主义”的标签。而事实上,我在写作时抱定的唯一主义就是“人”即“诗”。
安歌:所以我看到有评论说,你探讨的这些问题都是诗歌的本源问题,它们既宏大且是绝对绕不过去的,而企图以三千字左右的规模解释清楚,又冒着极大的风险和“亏欠”。故而你直接亮明自己的观点,并注重用简略、精当、通达的语言进行阐释,行文时放弃了学院派的寻章摘句和注释索引,也不涉及对具体诗歌或诗人的征录评价,给出的完全是一种总体性的、哲学性的探讨和思索,甚至倾向于古老心学的顿悟。
李瑾:思路是这样的。因为在我看来,“诗”始终存在/存活着,她是自成系统/生机的。你看,阿兰·巴迪欧说得多好:“诗的行动不可能是普遍的,它也无法成为公众的欢宴。诗歌把自身表现为语言之物,毫无例外的,作为一个事件被经历。马拉美谈及诗歌时说‘人为的,存在着,它全然独立地发生。’诗歌的这一‘全然独立,构成了语言内部的一场独裁起义。这就是为什么诗歌既不表达也不进入一般的流通。诗歌是叠合在其自身内部之上的一种纯粹。诗歌毫无焦虑等待着我们。它是一种闭合的显现。我们朴素的凝视展开它如同一把扇子。”
在“此岸”此时重启“诗”的本源之思
安歌:但萨特可不这么认为,他的《禁闭》将个体的“为他存在”置于地狱这一极端境地里来考察,地狱是什么?是个体经验到他人时萌生的原始感受。鉴于此,你如何理解他人?
李瑾:我的观点是,“‘诗’一直对人的异化保持警惕,尽管她自己也时时刻刻面临着异化。……‘诗’让自我发现了存在的奥秘:通过确立内在的我、精神的我,才能将人立起来。这种将‘诗’纳入社会关系范畴内进行分解并建构的企图,显然将‘诗’等同可人,将诗学等同了人学。由是,在‘诗’中重新发现和确立的主体性是属于唯物主义世界的,而不只是在单薄的意识世界中反而商榷。毫无疑问,对客体、事物的理解和理论概括,是不可能脱离主体性因素而孤立地达到的。”至于他人问题,我在《谭诗录》已经有所交待,大体意思是:“诗”包含了自我,也包含了他者,也就是说,内在个我是他者个我,他者是个我他者,“诗”的生成是个我和他者在自我中的对语。“诗”是一个心灵社会——既非无自我社会,也非无他者社会,在这个“社会”中,诸多主我基于一个共同平台而有了对话/吟咏的质性或可能。也就是说,在“诗”的形象世界/想象领域中有一个诗化的现实。
安歌:这倒切近博尔赫斯的理论思路,他说:“罗伯特·路易斯·斯蒂文森也提过……诗歌反而比较接近凡夫俗子及市井小民。他说,因为诗歌的题材就是文字,而这些文字也就是日常生活中的对话题材。……如果我们接受斯蒂文森的说辞,就产生了一种诗学理论——这种理论就是,文学作品所使用文字的意涵将会超越原先预期的使用目的。”
李瑾:若非如此,怎么理解目前的世界?但“比较接近凡夫俗子及市井小民”也会产生另外一个问题,我们通过“卑贱”的、物质的身体和他人发生关联,从而介入我与他人共在的世界之中。但这个世界并不全然是身体的,还是感知的,即它无时无刻不以影子/影像甚或信息的形式浮动于我们周围,因此,即使彼此并不相识,他的情感还是会紧紧包围着甚至俘虏了我们。
安歌:是的,谢默斯·希尼在谈到自己的作品挖掘时就说:“我是1964年夏天写的这首诗,几乎是在我开始涉猎诗歌两年之后,而正如帕特里克·卡瓦纳所说,一个人涉猎诗歌并且发现诗歌是他的生命。这是我第一次觉得我所做的不仅仅是文字排列:我感到我已掘进现实生活中去了。”说到这里,我倒认为你以诗人的身份而非评论人身份介入“诗”的内在逻辑挖掘,在“此岸”此时重启“诗”的本源之思,是一种很有意义的建设或架构。
李瑾:身份问题是“诗”最排斥的东西。考虑到个人的追求和努力,我愿意变化咱俩对话开始时的观点,“诗”是“人”唯一的“真”问题。约翰·塞里奥认为史蒂文斯作为一个诗人的伟大之处是在其诗中丰富地表达了自我,甚至说超越了自我:“诗人的任务就是将他想象的能量传递给他人。史蒂文斯认为,诗人只会在他看见他的想象力成为了他人的心智之光时才能感到满意。简单地说,诗人的角色就是来帮助人们过出自己的生活。”





 京公网安备 11010102004843号
京公网安备 11010102004843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