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离岸流》:小说的包容与自由
发稿时间:2020-07-28 13:10:00 来源: 北京日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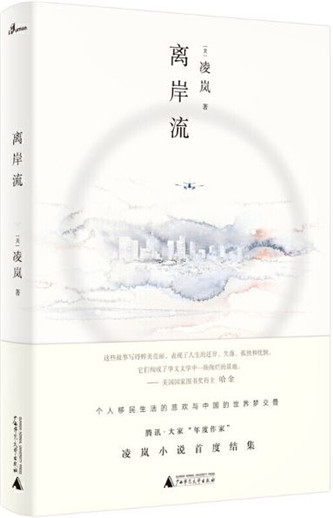
人到中年开始小说创作的凌岚,集诗人、翻译和时评作家于一身,也是我有幸结识的于古今中西小说广有研读的饱学之士。她的小说集《离岸流》最近出版了,作为其中多部作品的较早读者,我愿意谈谈自己的看法。
几乎每一个故事,都是“追寻”的故事
13部中短篇小说,主人公均以在美生活的华裔为主角,风格有的委婉低回,有的俊朗刚健,如果一定要圈出某个一以贯之的主题,或许就是“追寻”——几乎每一个故事,都是追寻的故事。
《冰》写了一对离异夫妇藕断丝连,登上奔赴南极探险的豪华邮轮,化解前嫌、重修旧好的故事。看上去,似乎是女主人公林里在寻求婚姻的破镜重圆,可是到了故事结尾,读者才恍然悟到,那个从题目至旅程,一直贯穿其中的近乎抽象的“冰”,才是女主人公追寻的象征——“伟大、冷酷,超越一切。跟这个无限的存在比起来,她人生的一切,完全微不足道。”这样的面对终极的灵魂觉醒,让林里于两性博弈中由被动转为主动,也使两人经历重重阻挠,彼此产生一点难得的陌生感和新鲜感,又借脆弱的性,来弥合支离破碎的关系。
《司徒的鬼魂》写林里在小镇偶遇印第安酋长后裔司徒,两人因丧偶、因病弱而同病相怜,进而由怜生情的故事。结尾处司徒披着祖先作法时候的白头鹰羽毛蓑衣一飞冲天,而林里则在“你要信”的嘱咐声里沉浸。“信什么”?小说没有给出明确答案。信某种宗教,信人人平等,甚至以小说为信仰——似乎都无不可。总之,要“信”,要追寻。
《桥水》叙述的是“我”陪伴亲人般的婉姨在美国小城寻找亲生女儿,却与女孩失之交臂的故事。婉姨是中国改革开放之后依靠个人奋斗成功的女强人,可她却有着难于启齿的隐痛——改革开放之初,为了当时难得的出国机会,哄骗年幼的女儿赴美,却不料从此失去了女儿。通篇的故事都在追寻,其实通篇也是对价值的追寻。
《桃花的石头》以插叙、倒叙的方式,写了两代、数位华人女性,面对婚恋、生育、职场乃至人生梦想时,往往顾此失彼的艰难选择。
这样的可以导源于希腊神话的“追寻”母题,在丰富华语移民文学内涵,尤其是丰富其中的女性形象方面,皆有可贵的探索与贡献。
“借景”式的双线叙事
明代计成在其造园艺术理论著作《园冶》一书中,提出了“借景”说:“……高原极望,远岫环屏,堂开淑气侵人,门引春流到泽。”又说:“夫借景,林园之最要者也。如远借,邻借,仰借,俯借,应时而借……”
现代华语小说之中,较早践行这种美学上的“借景”叙事的,当推鲁迅的《药》。而凌岚在《离岸流》多篇小说中的“借景”式双线叙事结构,又可细分为数种。
比如《一条名叫大白的鱼》,给我的阅读感受就是“远借”:有如隔帘观山,竹帘之内的近景——美国的现实生活、等待绿卡的煎熬,似乎还不是叙述的实际焦点,那最牵动人心的,是帘外的“远岫”,是从未于小说中露面的,因种种不得已、暂时无法去探望的垂危父亲。让我想起了国内千千万万如凌岚父母一样的长者,他们肩住了此岸生活沉重的闸门,放孩子到彼岸去追寻新天地、新可能。
《冰》里的“借景”:破镜重圆是近景,林里对自我的寻找,那个无处不在的终极却需仰视才见——那种借景是“仰借”。
写母女关系的《桃花的石头》,里面的借景手法当属“邻借”:女儿桃花的成长是面前的近景,母亲叶曦的经历是邻近的风景,近景邻景声气相通——是在桃花的回忆中;那真正的交会,则是腹中胎儿的去留问题——两人都选择了留住孩子。
而《蜜蜂》中的借景则是“俯借”:小欧父母的离异及其对孩子的深层影响,是要有如剥开地表枝蔓,向着盘根错节处层层深挖似的探寻。
不难看出,凌岚多次采用的“借景”叙事手法,或许尤其适合于移民文学——正如那句名言所说:“离开,是写作的开始。”移民文学写作者仿佛身处一座命运的巨轮,从母语国度驶向目的地国度,从一座城迁移到另一座城,故乡的风情与历史,途中的所见与所闻,直至新家的人情与世情……往往可以作为远景、中景与近景,交互切换、几厢映照,从而使读者在花窗式的剪裁中,窥见层层深远的风景。
“万物兴感”的拟题方式
说到拟题方式,《离岸流》一书的13篇小说题目,几乎每一个都不能僵硬地坐实。好像除了《啊新泽西!》之外,每一题目都蕴含了不止一层的寓意。比如《离岸流》既是指称结尾那股带走胎儿骨灰的海流,同时,又何尝不是指代了“我”和红雨这样从中国内陆来到美国闯世界的出国潮中的留学生?比如《枪与玫瑰》,既是那个作为礼物的乐队海报,又是柔丝与富商婚外情的象征,或是男女性事的隐喻;《必经之路》表面是写林里上班的必经之途,读到结尾才发现,那也是主人公悟出人生与爱之真谛的必经之路;《无尽里》既是“我”的父母所居街巷的名称,又象征了“我”对父母的思念;《桥水》,既是“我”陪婉姨去寻找女儿的目的地小镇,也是英文成语“桥下之水”,意即“已经过去的不可改变的事”;《带雀斑的鹦鹉螺》,以“我”对女儿讲解鹦鹉螺“是一个贪婪的捕猎者”作为开篇,以珍妮赠“我”鹦鹉螺为呼应,最后暗示珍妮对“我”的爱而不嫁或许隐含着性榨取的“捕猎”意味;《蜜蜂》则是借由小欧在与莉莉安郊游时候被蜜蜂蜇伤一事,暗喻了情欲有如蜜蜂之刺,在小欧的父母婚姻中伤人,也在小欧的内心触发“欲望”与“原罪”的冲突;《桃花的石头》,看上去是埋伏于结尾处被桃花怀着叛逆心理踢飞的石头,实际上还埋伏在小说的中间,借助“桃花的心里也是一块石头落了地”,来指代她腹中的胎儿——有助于本文具备更深的探讨女性自我觉醒的内涵;至于《一条名叫大白的鱼》,小说的写作动力虽是丧父之痛,拟题却引读者目光聚焦在“鱼”的身上,尤其是到了结尾,当大白率领着鱼群昂然出现的时候,这条锦鲤俨然成为一种生生不息的华裔移民奋斗精神的化身。
列举了上述的拟题寓意,似乎不难发现,凌岚这样的兼备诗人身份的小说家,在构思小说的过程中所具备的某种优势——那就是“万物兴感”:生活里任何一个微小之物,都可能作为触发,成为隐喻的外壳,成为诗心的外化。
说到诗心的外化,不免着重提到《无尽里》和《蜜蜂》这两篇,它们的“去故事化”,给我带来格外新鲜的审美享受,让人联想到契诃夫的《美女》等散文化小说。
阅读凌岚的《离岸流》,常常令我感悟现代意义上“小说”这个文体的包容与自由——它可以有着戏剧化故事化的果皮,散文情绪的果肉,诗心的内核。





 京公网安备 11010102004843号
京公网安备 11010102004843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