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人机协同生成
作为读者,很可能有过这样的想象:搬两把椅子,与作家相对而坐,目光是平视的,聊天是自由的。作家是作家,更是一个浸润在人间烟火里的普通人。
《文学的现场——作家说》一书,收录了我与30位作家的访谈文章,均曾发表于《中国青年报》“作家说”专栏,正是对以上想象的实践。严肃文学与类型文学,成名已久的作家与崭露头角的作家,都聚在了这个熙熙攘攘的文学现场。
这里的“现场”有几层含义:一是空间,作家笔下的文学根据地、他们的故乡与现居地,乃至访谈发生的地点,都构成文学地图的一个个标记点;二是时间,作家作品记录的年代,他们本人的童年与当下,都是流动而鲜活的;三是时空之外的种种集合,可能是一种情绪,可能是一种观点,让这个现场或许能建构一个文学意义上的完整世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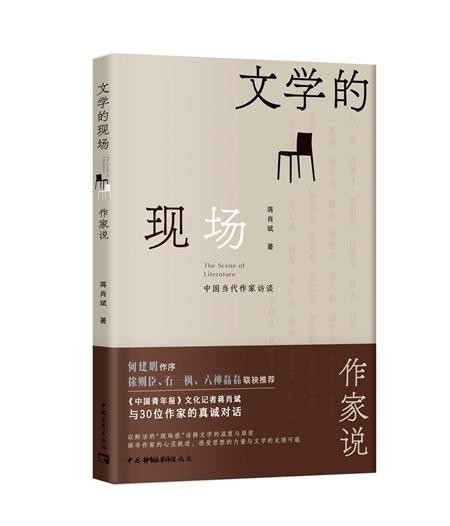
作家领路,打开文学的地图
很多作家笔下有一个相对固定的根据地,比如马尔克斯的马孔多、福克纳的约克纳帕塔法县、莫言的高密东北乡。在《文学的现场——作家说》中,作家领路,他们的文学地图被徐徐展开。
徐则臣的人生轨迹是一路“北上”,小时候生活在水边,18岁上大学又在运河边,20多年来,他写了很多关于运河的小说,比如“花街”系列,比如《北上》。第一次写花街,这就是一条南方典型的青石板路,几十户人家,门对门开着;后来再写,人物和故事放不下了,这条街就越来越长。有人问,这条街到底有多长?他答,这个世界有多复杂,它就有多漫长。
刘亮程出生、成长于新疆古尔班通古特沙漠边缘的一个村庄,凭借《一个人的村庄》而被称为“20世纪中国最后一位散文家”。他8岁时,父亲就不在了,母亲带着7个未成年的孩子,艰难度日。而当他成年之后回忆童年,一切苦难竟然都被化解了。他说,童年一场一场的风、一夜一夜的月光和繁星,草木,虫鸣,一个少年在村庄里无边无际的冥想和梦,成为他写作中最重要的东西。
梁晓声说,作家永远写的是“他者”,于是也就成了时代的书记员。石一枫说,新文学的基因在于它的批判性,从鲁迅、茅盾,到巴金、老舍,这种基因一脉相承,抹杀掉这个特质,就不是新文学了。
因此,书中有文学记录,也有文艺批评。而对作家来说,最终的文学地图是“中国”。
作为报告文学作家,何建明笔下的“现场”是文学的,更是社会的。从20世纪90年代揭露中国矿产资源危机的《野性的黑潮》、讲述贫困大学生问题的《落泪是金》、全景式描述高考的《中国高考报告》,再到《国家行动:三峡大移民》《非典十年祭·北京保卫战》《爆炸现场:天津“8·12”大爆炸纪实》等重大事件,约70部报告文学作品,是对中国40余年的观察。
小时候读的书,为孩子写的书
每个作家都曾是孩子,一代人有一代人的青春,童年、成长、梦想……这些都是永恒的话题。他们小时候读的一本本书、长大后为孩子写的一本本书,都隐喻着阅读的生生不息。
刘心武称自己小时候是一个“狂妄的文学少年”,12岁上初中后就觉得自己长大了,要看《人民文学》《译文》。1958年,16岁的刘心武写了《谈〈第四十一〉》,给《读书》杂志投稿成功。编辑以为他是一个老先生,居然来评论这么一本冷门的苏联小说。
张炜小时候生活在山东海边,海边有成片的防护林。那时候的孩子,在林子深处突然遇到一个老婆婆,会怀疑她是不是妖怪变的——这种冒险的生活就是童年。无数的故事已经被张炜稍加改编写进了作品里,但仍然有许多没有写过。
在很多作家的讲述中,童年对阅读的渴望,历历在目。
陈彦小时候生活在商洛的山里,家里没有多少书,大概10岁时才读到了第一本比较“大”的书《高玉宝》。后来到县城工作,陈彦住在宿舍,床上靠墙码着半人高的书,晚上就睡在书堆边。
付秀莹小时候,村子里连有字的东西都很少。邻居家窗台上放着一本杂志,可能还用来垫过酱油,她就站着津津有味地看。高中时,付秀莹在报纸上发表作品,收到很多读者来信,与她探讨对写作的看法、青春的苦恼,但她还在愁数学。
徐则臣小时候在农村,看的很多书是传来传去的,早就没头没尾。很多年之后才知道,哦,那是《金光大道》《艳阳天》……他看的第一本完整的严肃文学长篇小说是《围城》,小时候每个假期都会重新看一遍。不过,徐则臣“进步神速”,到小学五年级,已经把金庸所有的武侠小说都看了。
而以解读金庸小说为人熟知的六神磊磊,初中才开始读金庸原著,看的第一部是《神雕侠侣》。时过境迁,金庸武侠已成经典。六神磊磊说:“流行文化无法取悦每一代人,如果没有经受住时间的检验,它就消亡;如果经受住了,它就成为经典。”
作家在为孩子写作时,往往有明确的站位和价值取向。他们深知,童年时期的阅读将会影响一个人的一生。
肖复兴小时候喜欢读现实主义的小说,比如瓦尔特·本雅明的《驼背小人》、帕乌斯托夫斯基的《一生的故事》,觉得和自己所认识的现实生活接近。很多年以后,他在少年成长小说《兄弟俩》中回望自己的童年。他并不希望孩子只读儿童文学,他认为,挑选一些经过时间筛选、值得信赖的成人文学作品去读,是十分必要的,“阅读层面需要踮一踮脚尖、蹦一蹦高”。
这30位作家中,在孩子中知名度最高的可能要数沈石溪。被称为“动物小说大王”的他,40多年写了70多种动物。他笔下的故事,从不回避“丛林法则”。沈石溪认为,高年级孩子阅读的小说,应该有限度地接触真实的生活、真实的社会。
孩子读什么,没有唯一答案。但有一点可以确定,正如沈石溪所说,书中始终要向孩子们表达的主题是:美好的东西、生命的力量,不会随着个体被消灭而烟消云散,它会变成一种精神上的基因,代代传承。
作家来来往往,你我亦在其中
跟随作家的作品徜徉过文学的地图,也跟随作家的记忆回溯过童年的阅读,最后,还有一块作家的“自留地”,可能是读者日常接触不到的。书中,那些无关文学、有关生活的话题,让“现场”的氛围感更浓郁了。
“斜杠青年”可能是个新词,但“斜杠”似乎是任何年代作家的常态。比如,20世纪80年代的“先锋作家”马原做过记者、编辑、教授、商人;在20世纪80年代度过童年的路内,做过化工厂工人、仓库管理员、广告公司策划;刘庆邦当过农民、下过矿井;刘亮程开过农机配件门市部和酒吧……
看来,作家的日常和我们一样,没有“主角光环”,一直在尝试,在挑战区与舒适区之间徘徊。余耕曾自诩是打篮球里小说写得最好的,但不巧有一天遇到了冯骥才先生。没错,即便在这30位作家中,除了写作之外的行当,作家们也能“卷”起来。
作家在写作之外的“闲趣”,与他们笔下那些文学的爱恨情仇、那些历史的悲欢离合,搭配参照,碰撞出一个个活色生香的现场。
叶广芩爱吃,只要出门,就必须找地方特色尝尝,什么时令吃什么,比如春天的香椿正当季,搁点儿盐、醋、香油,再不放别的;陈彦是一个天文爱好者;邱华栋练过武术,喜欢极限运动;李修文喜欢树,一棵苗木多少钱买进来、苗圃里养几年出圃能卖多少钱,他一清二楚。
徐则臣回忆,大学毕业后他成了“北漂”,在杂志社做编辑,一开始一个月工资1500元,房租就要花掉1100元。那时候特别向往的,就是每周或者每两周一次,到人大西门外一个小馆子吃重庆水煮鱼,“豆芽在用过无数次的油里煮过,特别入味”。
年轻,似乎天然包含一种乐观主义,从来如此。
“作家访谈”能让读者迅速了解一位作家和他的部分作品,而我更希望的是,阅读能成为日常,作家来来往往,你我亦在其中。
中青报·中青网记者 蒋肖斌来源:中国青年报
2025年04月25日 07版





 京公网安备 11010102004843号
京公网安备 11010102004843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