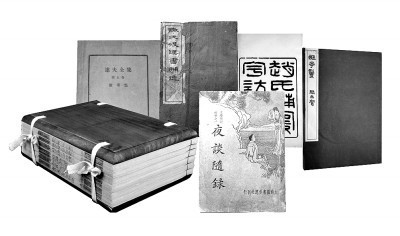
《夜谭随录》《痴华鬘》《补寰宇访碑录》等古旧书。资料图片
【藏书记】
一
二十世纪八十年代末,我在鲁迅博物馆参与《鲁迅研究动态》的编辑工作。那时候,这本学术研究杂志的日常业务主要由鲁迅研究专家王世家负责。王世家朋友甚多,信息来源亦广,也搞收藏。他藏有不少名人手札,如茅盾、叶圣陶、端木蕻良的,十分珍贵。与他往来较多的诸多鲁迅研究学者,不乏藏书家,如唐弢、林辰、姜德眀等。我也是在这个时候,开始注意到一些学者的藏书,并对许多长者的书房产生了好奇心。
二十世纪九十年代,我多次去过林辰、姜德眀的家,才知道他们藏书的品位之高。林辰的房间不大,四处都是旧书,除了书架是满满的,床底、窗前都是老期刊与出版物。姜德眀书的数量不亚于林辰,藏书的条件好于林辰,一些珍贵的版本放在墙上的吊柜里。林辰与姜德明是好朋友,他们之间围绕书籍的版本有不少交流。彼此谈论最多的,是关于鲁迅著作的校勘、注释之事,兼及现代文坛中各类人物遗稿的整理。现在想来,二人的来来往往,算得上学林佳话。
林辰出生于1912年,长姜德明17岁,他们什么时候认识的,不得而知。王世家后来编辑的《林辰文集》,材料丰富,有十五通致姜德明的信,看得出他二人相知甚深。姜德明的收藏与林辰的趣味接近,鲁迅书籍的初版本很多,他知道林辰也有不少宝贝,彼此也就互通有无。他们常常在一些会议场合见面,住在宾馆时也常常分享各自的版本之乐。1986年4月,姜德明知道林辰在研究鲁迅辑校的古籍,但林辰手中缺《痴华鬘》,便把自己的这本书寄给了林辰。林辰回信道:
“承赐原版《痴华鬘》一册,已收到了。古人常说的‘赐我百朋’,表述不出我的感谢与高兴!我搜集鲁迅先生作序或编辑、校订的书,只收原版,已得十之七八,《痴华鬘》是我搜寻已久而今日始得到的。”
1989年1月9日,林辰在致姜德明的信中谈到自己想阅读的几本书,有借书的意思:
“我没有《文学姻缘》,但亡友孙用先生有此书,我曾经在他的书斋里见过,确系绿面金签,如鲁迅先生之所说。您所藏的一册,若不是一九○八年东京初印本,那就是上海群益书社的翻印本了。据柳亚子先生说,群益本没有载明出版年月。至于您介绍女师院线装讲义本《中国小说史略》的文章,我还没有见到。
大著《书味集》中有一篇《鲁迅与寿石工》,其中提到高伯雨的《听风楼随笔》一书,我曾读过高的文章,很想看看这本《随笔》,但香港出版的书不易见到;您如有(或报社图书室有),能惠借一阅吗?”
看这些尺牍,能够嗅出书香之气,还有学者的功底。林辰虽然自己的藏书很多,依然觉得所知甚少。在他致朋友的信件里,能够体察到他的阅读需求,以及治学尽精微的态度。他与姜德明谈论古代版本的优劣,有文献学的底子,因此能在不同版本中发现一般人注意不到的遗存。
林辰个子不高,一口贵州口音,为人温文尔雅,看上去就是书斋之人。他每到鲁迅博物馆来开会,年轻一点的人都会问他一些掌故。他言之甚简,而每每直指要义。有一次我与黄乔生编辑“回望鲁迅丛书”,向他请教一些技术性的问题,他都一一答复,对我们的编辑思路不无启发。他去世前,决定把自己的书都捐献给鲁迅博物馆。他逝世于2003年非典期间。那年10月,我与几位朋友一起到他家中,把他的藏书拉回博物馆。有的藏品之好,填补了博物馆资料收藏的空白。如今想来,亦觉感慨良多。
二
在整理林辰的藏品时,能够感到他学术功底之深厚。
林辰熟悉经史子集,且心得颇多,《鲁迅全集》涉及古籍的部分多是他负责编辑的。由于其旧学修养好,保证了全集的质量。他的线装书很多,其中不少清刻本,有的是贵州史料,更多的是与鲁迅有关的书籍,如《夜谈随录》《敝帚集》《补寰宇访碑录》《谢氏后汉书补逸》等。
他的藏书中,鲁迅著作的初版本也很多,比如《域外小说集》《中国小说史略》《小说旧闻钞》等。与鲁迅有过交往的同代人著作的初版本数量更为可观,包括高长虹、许钦文、向培良、李霁野、韦素园、萧红、萧军、柔石、叶紫、王鲁彦、彭家煌等人的著作。藏书中的签名本也很多,如许广平、沈从文、郑振铎、孙伏园、冯雪峰、唐弢等人的签名本。这些藏书,显示了他进行鲁迅研究的多种向度:一是梳理鲁迅的文本与鲁迅涉猎的各类知识;二是整理鲁迅与同时代人的交往及相关痕迹;三是研究鲁迅思想传播的轨迹。因此,他的收藏,是有目的的收藏,是对他的学术研究和《鲁迅全集》的编辑助益良多的收藏。他发出的鲁迅是百科全书式的人物的感叹,不仅源于他对鲁迅文本的认知,也与他触摸到了鲁迅的“暗功夫”有关。在鲁迅研究学者中,他是国学根底最为深厚的几个人之一。
前辈学者曹聚仁、王瑶、李何林对林辰都颇为佩服。曹聚仁还说,林辰是写《鲁迅传》最好的人选,因为他取材准确、考证细腻,且在学问上可以与鲁迅对话。我以为,这是颇为恰当的评价。二十世纪三十年代,《鲁迅全集》还没有出版的时候,他就考证得出了鲁迅一些行迹的确切时间,而且都与鲁迅日记所载吻合。他还从周作人、许广平、许寿裳等人的回忆录里发现了史实性的错误,能够从众多文献里看出蛛丝马迹。比如,李长之的《鲁迅批判》有一些史料方面的硬伤,他大概是最早提出来的。林辰对章太炎、严复、苏曼殊、吴虞、沈尹默等都有研究,他看待这些人物的标准,主要参考的是鲁迅的观点,立场颇为鲜明。从他写于1945年的《人品与文品》一文中,可看出他对易节的士人是有一些微词的。他身上的气节,从他的文字中能够感受一二。
我最喜欢他谈论鲁迅古文修养的文章,比如鲁迅抄录的《沈下贤集》、编辑的《唐宋传奇集》,他都能体会其中治学精微之处。他在《鲁迅计划中〈古小说钩沉〉的原貌》一文中所涉古籍之多、看法之中正、笔触之老到,非一般学者可及。鲁迅整理、阅读的古籍多矣、杂矣,比如《云谷杂记》《百喻经》《游仙窟》等古书,如何被鲁迅注意到,林辰看法都颇为精准,这与他自身也藏书是分不开的。我在写《鲁迅与国学》一书时,对魏晋文学及典籍的理解,有些地方来自他的文章。在治学方面,林辰藏书亦研究书,重证据、重考订,身上有乾嘉学派的影子,而他行文里的思想,却是五四式的。这使他虽深泡在旧书里,却没有遗老气,文字有活力。
三
王世家生前谈到林辰,十分佩服,两个人围绕藏书之事有过不少交谈。他还请林辰写过访书、写书的经历。只是林辰犹豫了许久,迟迟没有交稿。这大概缘于他不太愿意谈论自己,以为自己是寻常之人,不足为道。最后,在朋友诚意邀请下,他还是写了《瑯嬛琐记》一文。文章回忆了他在重庆米亭子,上海城隍庙,北京隆福寺、东安市场等地的访书经历,读起来很是有趣。他认为,“访书也如读书一样,要手到、眼到、心到,还要加上一个脚到”。回忆自己在东安市场和西单商场淘书的经历时,他写道:
“五十年代,我每个星期日几乎都消磨在这些地方,平时白天上班,晚上就轮换着去,流连忘返。常常是毫无所获,只弄得两手尘土,一身困倦,但对各书店寻览一周,随便翻翻,也自有一种乐趣。有时发现一本两本心目中正需要的书,那高兴自然就不用说了。夜市既阑,挟书以归,要是冬天,穿过一条条小胡同,望着沿街人家窗户透出的一线光亮,抚着怀中的破书几帙,只觉得灯火可亲,寒意尽失。”
第一次读这段话,我便感到他的藏书里满是故事,每一本书细说起来都折射着不同的心绪。在鲁迅博物馆工作的那些年,我常到资料室翻看林辰所捐献的各类书刊。翻看之时,心中涌起的惊奇、感叹、兴奋之感都有。比如他藏的一些文人绝版著作,在一般的图书馆都不易见到。我后来写一部专著时,对二十世纪三十年代文脉变迁的梳理,一部分就借助了“林辰文库”里的资料。有时我思考文学史的细节,对照他的文章,如在山野迷路时忽然见到路标,快慰感随之而至。倘若没有这路标,暗中摸索会走许多弯路。
读书人以藏书为志,虽是始于个人兴趣,但其中求知以望道的路径,对于他人而言,也是有借鉴意义的。
(作者:孙 郁,系中国人民大学文学院教授)





 京公网安备 11010102004843号
京公网安备 11010102004843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