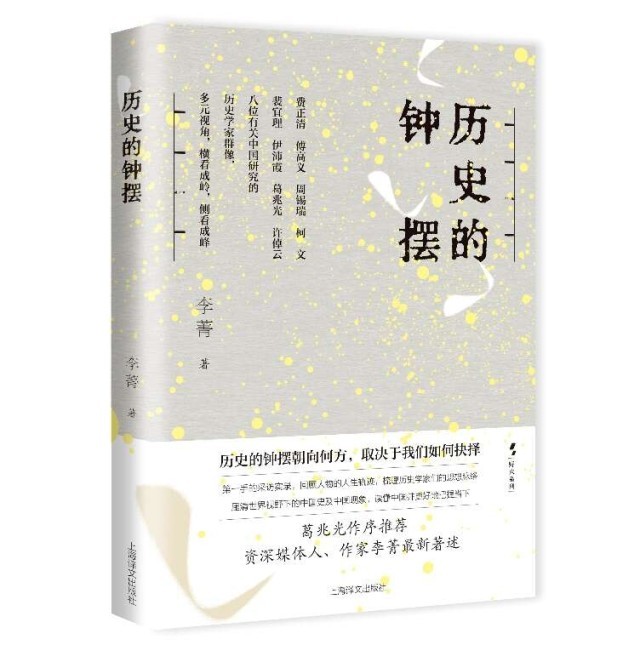
《历史的钟摆》封面。出版方供图
马子倩
离别常常猝不及防。7月初,资深记者李菁的新书《历史的钟摆》出版,书中收录了近些年她为多位中外学者所作的访谈集。前几日,许倬云先生在美国去世的消息从大洋彼岸传来,让书中在世的主人公又少了一位。
李菁是在2021年赴美国加州大学圣地亚哥分校访学期间对许倬云进行的采访。彼时,91岁高龄的许倬云尚能灵活地操纵着轮椅在匹兹堡的公寓里“穿梭自如”,但因为身体先天的残疾,让他始终对生命满怀忧患。
从早年研究上古史和秦汉史、写下“中国古代三部曲”,到晚年着眼于大历史,“要从世界看中国,再从中国看世界”,用许倬云自己的话说,这“一方面是对中国的关怀,更大部分是对全人类的关怀”。
许倬云曾在自己的书中批评西方现代文明的弊端,疾呼建立中国的现代文明秩序,有读者认为他的判断被“家国温情遮蔽”,这位生于战乱岁月、历经海峡和太平洋两岸时局变化的老人直言,他本意并非主张民族主义。
基于对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西方社会所经历的种种挣扎与困境的深入观察,许倬云逐渐意识到,当下的西方展现出了与其过往形象截然不同的一面——这一面,是此前在西方留学的中国学者鲜少接触到的。这种认知的转变,也促使他对中国的看法有了更清楚的认识。
于是,“交融”成了许倬云做学术的关键词,既研究中国黄河和江汉流域的互动,关照中国不同族群的演变,更致力于让东西方的观念融合得“更合理、更完整”。
他说,“我将‘最大的全人类’与‘最小的个人’这两个项目视为真实不虚的东西——国也罢,族也罢,姓也罢,都是短暂或局部的,经常变化。哪个国的疆域没有变过?哪个族是永远这么大的?哪个姓没有经中间变化而来?哪个地方是永远同一个地名?哪个村永远是同一批人?所有这些设定,都是变化的。”一连串反问,足见其视野之大。
许倬云以“学术界的世界公民”自居,尽管这一身份“非典型”,却使他如同书中其他外国学者一般,以一种“他者”视角来审视中国。
“他者”是相对的,最近,因主编《从中国出发的全球史》而活跃在公众视野中的复旦大学历史系教授葛兆光,其访谈内容也收录在此书中。葛兆光对自己的定位是“守住历史的边界”,只“诊断病源”,把“开刀动手术和开药方”的工作交给政治家。
这本书重温几代美国学者对中国土地的深情、对中国研究的投入,以及为推动两国往来作出的努力。“你喜欢一个国家,喜欢一个文明,喜欢他们所承载的文化,研究这个国家,那才有意思。”师从费正清的美国加州大学圣地亚哥分校教授周锡瑞这样解释自己在冷战时期选择投身中国问题研究的原因。
这些美国学者几乎一辈子都在学术圈里驰骋,但却从未陷入困守象牙塔的困境。目光抽离当下迷局,投向过去半个世纪的风云变幻,他们的个人生活紧密地和时代联系在一起。
裴宜理1948年出生于上海,之后全家离开中国,直到1979年中美关系解冻,这位“出生在红色中国”的美国女性,才重新回到中国。
值得一提的是,书中诸多关于美国学者的叙述皆以家庭为脉络展开。不少人的父辈故事便起始于中国大地,许多人在中国结婚生子。根据费正清的回忆录,1943年,他通过私人渠道为西南联大的全体教员运来药物。如此种种,为那战火纷飞、动荡不安的年代,增添了动人的温情。
不知是否是巧合,李菁做了20年记者。在她的笔下,很多汉学家的人生转折都和记者有关。
1943年,费正清经由时任美国《时代》周刊驻华首席记者、也是他的学生白修德介绍,认识了周恩来的新闻发言人龚澎,并由此展开与中共高层人士的往来;在犹豫该选择什么题目帮助美国人了解亚洲发展时,是一位专门研究东亚问题的记者建议傅高义把目光锁定在邓小平身上,这才有了后来享誉世界的《邓小平时代》。
至于周锡瑞转向“社会史”方法论的缘起,则可追溯至1965年,当时,他在父亲的帮助下,以《旧金山纪事报》海外记者的身份去到了越南战争一线。
回到许倬云先生身上,他在访谈中提出,希望“找到中西如何互相调试的途径”。这呼应了书中一位编辑的话:“历史的钟摆朝向何方,取决于我们如何抉择。”





 京公网安备 11010102004843号
京公网安备 11010102004843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