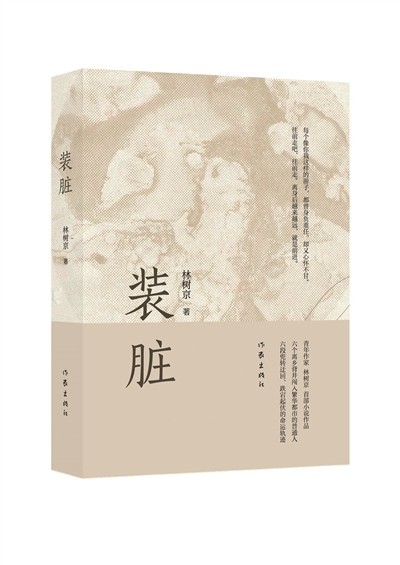

作为新人首作,林树京没想到他出版的第一本小说《装脏》在豆瓣上收获了7.8分。此外,这部小说还先后登上《出版商务周报》月度价值新书榜、“探照灯好书”月度中外文学佳作榜等权威榜单。林树京也凭该作荣膺2025当当年度影响力青年作家。
近日在接受北京青年报记者专访时,他坦承“能得到这样的关注和评价,远超我的预期”。
林树京告诉记者,自己经常看读者的评论,很多评论会让他陷入思考。让他印象最深的一条是“看完这本书,我也想回头看看自己的身影”。林树京说看到这条评论的那一瞬间,感觉这本书已然成了一个介质,“让我和那么遥远又陌生的一个人的人生有了联结,这样的感受太奇妙了。以前我都是抱着表达自己的心态来写作,但看到这个评论,我就突然意识到,或许我可以像很多作家一样,用作品给别人带来力量、带来思考。”
至于期望读者可以从书里得到什么力量,林树京表示对作者而言,“读者能够翻开你的书已经是莫大的荣幸,所以我会希望他(她)能够收获一段美好的阅读时光。当然如果有读者发现‘这说的不就是我嘛’,继而感到一种被理解的释然,那就更好了。人的力量,往往从‘原来我不孤单’开始。”
壹
人到中年 不吐不快
《装脏》由六个故事构成,分别为《装脏》《坠落》《空游》《手中之海》《红土路》《夫人妈》。这六个故事各自独立又相互关联,几位主人公在故乡与异乡之间兜转前行,串联起一代人的漂泊群像:怀揣电影梦的青年林北树,一心想要在北京扎根,他以故乡为原点却始终逃不开乡愁的坐标;话题女星宋飞仙逃离都市,藏身于山谷,只为寻找理想中的世外桃源;喜剧大咖郝幽默接连票房惨败,回到家乡的庙宇,不求事业顺遂只想找寻打开旧居的钥匙;背井离乡的许阳放弃跳水梦想,却在异乡的地下室坠入生活的死水;一生被束缚的农村女孩秀惜,带着满身的伤痕从家暴中逃离……
六人以故乡为起点,逃离、兜转、踉跄前行,被生活的浪头一次次打翻。虽然前方的终点尚不明确,但他们始终没有放弃夺回自己命运的主导权。
80后的林树京毕业于兰州大学中文系,在影视行业工作多年。被问及创作初衷,林树京说并非为了圆文学梦,而是源于一种“不吐不快”的冲动。“人到中年,目睹也亲历了太多痛苦的瞬间——为了生存、为了别人的评判、为了那点可怜的梦想或尊严,不得不活成自己不喜欢的样子。这种情绪如鲠在喉,像一块顽固的石头。”写作,于他而言是理解它,也是将它从心里掏出来的过程,“看看它究竟长着怎样的棱角”。
《装脏》的六个故事,林树京并非一开始就规划清晰,“我是不管三七二十一,先动笔再说。所以初稿写出来后,是一个结构很凌乱的长篇小说。”修改的时候,他意识到,如果把一个长篇拆成几个中短篇,可能在阅读体验上会顺畅一些,“就大刀阔斧地改了,所以这六个故事不是同时蹦出来的,更像是在同一个故事下生长出的不同枝丫。这些故事,有些源于生活中一个强烈的意象,比如郝幽默的钥匙、秀惜的签诗;有些源于对某个群体生存状态的长期观察,比如娱乐圈边缘人;有些则是对某种情感困境的感受,比如许阳和父亲、林北树和宋飞仙之间的情感。这些‘种子’其实很早就在脑海里生根发芽,在写作时,才逐渐找到适合承载它们的人物和故事脉络。”
贰
究竟要向自己的内心装入些什么 才能真正找到归属感与满足感
“装脏”原本是一个佛教概念,指为新佛像装上象征性的内脏与神识,赋予佛以生命力。在小说中,“装脏”被巧妙地转化为对人物内心世界的隐喻,象征着人们把自己最珍贵也最痛苦的记忆藏在内心深处,如同神像背后藏宝贝的空间。
例如郝幽默的奶奶把家里的钱及贵重物品装在佛像背后的肚子里,郝幽默把家里的钥匙放进庙里尊神的肚子里。同时,“装脏”也象征着给予事物灵魂,代表着每个人在生活中所背负的情感与理想的“行囊”,提醒着人们思考在追寻成功的道路上,究竟要向自己的内心装入些什么,才能真正找到归属感与满足感。
六个故事中,林树京一气呵成写得最顺的,是郝幽默那篇,写得很痛苦的是秀惜那篇,“那时候我给自己定了个目标,一天至少要写1500字。但写着写着发现总是完成不了任务,因为写得太入戏而太难受了,整个心是揪着的,必须要停下来缓缓才行。最后写了将近两个月才写完。”
而在他看来,最难的则是开始动笔,“最早有想写书的念头是高中时期,我十七八岁的时候,但是真正动笔已经是2015年,我创业第二年。那一年我曾经尝试过,记得是国庆假期,我老婆很支持我,为了给我一个清静的环境进入写作状态,特地带孩子回娘家待了一段时间。但刚创业确实忙,没有精力、心力,只是浅浅构思了一下,就搁置了。直到2022年,公司的业务按下了暂停键,才终于有了时间思考,也才终于正式动笔。”
《装脏》最后的定稿和初稿,差别非常大。林树京说写完《装脏》的初稿,他读到了诺贝尔文学奖得主石黑一雄的《长日将尽》。“这本小说写的是一个英国管家,在人生的暮年,认识到他的一生一直遵循着一套错误的价值观;认识到他在某种深层意义上浪费了人生。《长日将尽》给了我很大的触动。从管家身上,我看到了自己的影子。我这一路按部就班,不停地追求所谓的世俗意义上的成功,但却很少感到真正的快乐。”
读完《长日将尽》,林树京决定推翻初稿重写。“《装脏》原本的书名不是‘装脏’,结尾也不是现在这样。原本结尾是林北树找到了那条‘正确’的道路,意气风发,得意洋洋,他从未认识到自己‘在某种深层意义上浪费了人生’,也浑然忘记了那个他从不愿意正视的自己。重写的时候,我就想让林北树知道,他应该有所反思,这样的人生是不是自己心里所想要的。所以是石黑一雄改变了这本小说,也改变了我对于人生的一个态度。”
小说已经出版,林树京却难忘自己开笔的时候,“我没有书房,是在我家地下室的一个狭小逼仄的储物间写作的。一个小桌子,一台电脑,密闭的空间。旁边堆着玩具、行李箱、衣服,之前储存的大米、泡面、罐头。但我坐到电脑前,却感觉身处一片旷野,内心非常的自由。在那里,我敲下第一句话:我18岁那年,家门口有条土路直直通往村供销社,路边种着成片的针叶树木麻黄。开头写的《红土路》这个故事,后来放到了全书第五篇。”
叁
以真实出发 故事才会流淌出来而不是设计出来
《装脏》中对娱乐圈的描写真实生动,郝幽默、宋飞仙这两个明星的故事更是让人唏嘘。因为林树京是影视圈内人,难免有读者好奇小说人物的真实性。
谈及此,林树京坦承自己有点后悔用第一人称来叙事,更后悔给主人公取了林北树这个名字。“因为主人公和作者的名字太像,确实很多读者会代入,会误以为这是我的自传或回忆录,其实这纯粹是因为我有取名障碍。写完初稿后,我其实想过给主人公改个名字,但又很犹豫,因为书里有一段对话提到这个名字,说:‘生在南方,却叫北树,好像注定了要连根拔起,挪到别处似的。’如果改名,那这段对话就得删掉,我舍不得删,所以决定还是不改名了。”
每个作者在创造自己的主人公时,都难免会给笔下的人物套上一些自己的情绪、情感,林树京坦言自己也是,但仅仅限于情感投射。“在人生经历上,我跟林北树没有太多的关系,也没有经历过他那些情感纠葛。事实上,我把林北树塑造成了一个不完美的人,甚至是一个很讨嫌的人,不时地在故事里展现他的困惑、慌张、无助、懦弱、贪婪以及人性里丑恶的部分。我希望借助这个人物去探索人性,如果在他身上有太多我自己的影子,可能就下不了这个手了。”
至于人物原型,确实有很多人来问他,尤其好奇宋飞仙、郝幽默是否有原型。林树京笑说:“当然不是啦。如果硬要说的话,可以这么理解,书里每一个人物的性格和命运,的确都是基于现实的。只不过是综合了我身边很多人的性格,最终才提炼出来成为书里的一个人物。所以我也希望读者在看这本小说的时候,能够从不同人物的某一个剖面里,找到自己的影子。”
至于如何平衡“真实感”与“戏剧化”,林树京说自己不会在创作人物的时候,先去预设可以有怎样冲突的情节来勾住读者,他希望能够从人物的真实底色出发,顺着人物的人生轨迹和精神脉络去完成故事创作和人物塑造。“当人物活起来的时候,是没有办法用任何写作技法来干涉他的人生的。以真实出发,故事才会流淌出来而不是设计出来,才会自然而然迸发出很多有魅力的情节。”
写娱乐圈人物,林树京说不是为了展现他们的被“妖魔化”,也不是为了猎奇。“故事里所有娱乐圈的人,剥掉那层光鲜的外壳,都是普通人。比如宋飞仙,她的内里就是一个陷入困境的年轻人,我希望这个人物能折射出当代年轻人,尤其是女性在面对困境时的那种抗争。”
林树京表示,娱乐圈在很多人眼里,是光鲜,是梦幻,但在他看来,它是现实主义,有很多特别值得书写的地方,“有觥筹交错的往来,有上升的各种手段,有华丽的袍子底下布满的虱子,以及数不清的人情世故。有人看八卦,有人照镜子。我把小说里两个主要人物的职业定为明星,有这方面的考量。郝幽默和宋飞仙都是从底层、贫困的地方走出来的,也许是搭上了时代的顺风车,也许是搭上了行业的便车,当然也经过了个人很多努力,他们的生活发生了翻天覆地的改变。从这个角度来讲,郝幽默和宋飞仙跨越了鸿沟的人生,其实是不少80后、90后在时代里的一个映照,也能够契合很多人从泥泞中走出来,登上山巅却又甩不掉脚底泥的那种感受。”
肆
希望自己写出关于背井离乡的“答案之书”
《装脏》中说:“从某种层面来说,我们所有的情绪,所有的爱和恨,都根源于故乡。”书中对故乡的描写很微妙——它既是游子的精神寄托,又因现实变得陌生。这种感受是否与林树京自身的经历有关?
林树京表示,“最初塑造你的,是故乡。一旦离乡在外,就意味着你不得不改变,不得不接受新的塑造。而这种新的塑造,锥心刺骨却无人知晓。这时我们就得去寻找,让你痛苦的根源是什么,解药又是什么?”
作为80后,林树京认为他这代人,以及当下的很多年轻人,为了生活,或者为了梦想,都是逐草而居、精神“游牧”的。“漂泊仿佛是我们这代人要共同面对的命题,在城市化进程加快、人口迁移的速度和范围都在不断扩大的背景下,城市和乡村之间的界限越来越模糊。人们内心深处那种对‘家’的归属感,也变得越来越复杂,越来越难以捉摸。可以说,我们这代人,是被时代的洪流裹挟着去往陌生的地方,开启一段又一段看似充满机遇却又非常孤独的旅程。我在书里写到了:城市拥挤又孤独,在乡村我们却也同样无可依偎。但是我也一直在自问:离乡者在外,在饱尝‘闯荡’与‘孤独’交织的漂泊感后,如何才能自我和解,家乡是不是唯一的解药?”
林树京说自己对家乡的情感是流动的,“有时候它让你觉得思念、不舍,有时候又让你想要逃离。这种流动的情绪,其实也贯穿在我写作的过程当中。书里的很多人物,包括林北树、郝幽默等等,都是处在一种想回家又不甘心回家,想走出去又不甘心没了根的一种状态。”
而在离家以后,家乡在实际生活里占的时长会变得很短暂,更多的是在念想中存在。“在这种状态下,你回乡的短短的那段时间里,所经历的人和事就会被你反复地咀嚼反刍,那些美好的感受会跟着放大,不美好的感受也会拉长。这就导致确实有时候,你对家乡的情感,它不仅是流动的,甚至是疾风骤雨的,像过山车一样忽上忽下的,所有的情绪都会被放大。”
写《装脏》之前,林树京对故乡的心态是当局者迷;写了之后,他对故乡的心态是旁观者清。“写作的过程实际是让我跳出来,让我有一个旁观者的心态,我希望自己能写出一本关于背井离乡的‘答案之书’。我希望这本书能给读者提供一个新的角度,去重新审视自己和家乡的关系,能给予读者小小的力量,去改变那些令人焦虑不安的现状。”
伍
你所追求的 必须是你真正所想要的
写完《装脏》,林树京最大的收获是“理解”。“一方面更深刻地理解了人在困境中的选择、妥协和韧性,对生活、对人性中那些暧昧的地带,多了份理解,少了些苛责。另一方面是来自读者的理解,我看到大家在书评里分享自己离家的故事、异乡的艰辛、原生家庭的困境、背井离乡的不安,书里很多隐晦的表达和细小的心思也被一一挖掘出来。因为这本书,我拥有了很多的云知音,读者们给出的反馈,远比我期待的还要真挚。”
写《装脏》以前,林树京经历过很长一段时间的中年危机。写完《装脏》,他发现所谓的中年危机消退了很多。“最大的感受是不那么焦虑了,以前会因为要满足他人的期待、追求事业成功而焦虑。18岁以前,我以为父母的禁锢是一座大山。18岁以后,我离家去上大学,以为那一刻就剪断了父母的掌控。按部就班活到40岁,我才发现那座山根本没有移开,我每一步选择都不自觉地在完成世俗的期许,按部就班地毕业、工作、组建家庭、创业、搞事业、承担家庭责任,无暇顾及自己内心的诉求,直到把自己关在地下室写书的那两年,我才算真正斩断了自己精神上的那根脐带。”
林树京说那两年的写作,对他来说是回望和反思。书写出来后,自我认同的感受非常强烈,同时焦虑被抚平了,更从容了,不会再被别人的标准绑架了,更不会再用别人的眼光来塑造自己。
因为心态发生了变化,林树京说他的生活也有了很大改变。“变得自洽了,心态非常平和。有一件小事,几年前我女儿要填个表格,问我家长的‘职业’一栏要怎么填,我一时半会儿竟没想出来答案。写艺人经纪、宣传或商务吗?写传媒人吗?还是写自由职业?感觉都不太对。那时候我就觉得我的职业定位或者说人生定位出了问题。上个月,孩子放假了,我跟她一起收拾书包,发现一张卡片,上面同样有家长职业这一栏,我看她写的是‘作家’。虽然我并不认为自己已经是作家,作家二字只有那些功成名就的大家才配得上,但是女儿写的这两个字,的确给了我很新奇的感受,有种找到了人生定位或者说人生目标的感觉。”
林树京希望自己能够坚持写下去,“《装脏》出版前,我就开始写第二本小说了,现在已经完成初稿,正在修改。和《装脏》一样,第二本的修改也是一个非常痛苦的过程。第二本是个长篇小说,讲的是闽南红土地上的故事。”
写作分走了很多原本应该用在工作和生活上的时间,但林树京说自己觉得心满意足,“因为我正在用我喜欢的方式生活,所以我想借用书里的一句话,给那些正在经历中年危机的朋友:你所追求的,必须是你真正所想要的。化解中年危机,只有一个办法:勇敢去追求你的梦想和你真正想要的生活方式。”
文/本报记者 张嘉





 京公网安备 11010102004843号
京公网安备 11010102004843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