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青报·中青网记者 蒋肖斌
近日,北京观中观书殿内,作家路内长篇力作《山水》新书首发。南京大学教授、茅盾文学奖获得者毕飞宇与路内对谈,走进这部跨越半个世纪的家庭史诗。
小说以克制的情感、精巧的结构,讲述司机路承宗与妻子周爱玲从抗战烽火到改革开放时代,横跨五十载的生死相守,辅线铺展收养5个孩子温情与欢笑交织的往事,以一个特殊家庭的冷暖悲欢,折射出半个世纪中国的变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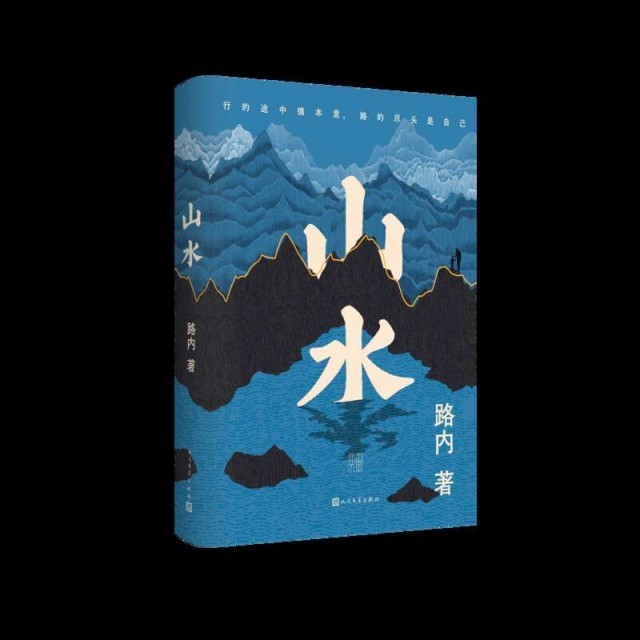
《山水》书封。人民文学出版社供图
如果说路内早年的《少年巴比伦》带着青春期的躁动与不羁,那么《山水》则展现了一个作家步入中年后的沉稳与深邃。
《山水》选择司机路承宗的一生这一鲜为人知的视角,来观照中国现代化的进程。小说细致描绘了从美式雪佛兰、道奇到德国朋驰、苏联嘎斯等各种车型,每一种汽车都代表一个时代,也象征着人物命运的起伏。
路内说,路承宗的原型正是他的祖父:抗战时开道奇卡车支援前线,抗美援朝时遭遇美军飞机却奇迹生还,连“见血要换轮胎”的祖训,都源自家族真实的司机传承。
这些藏在长辈口中的故事,让路内记了几十年。祖父在朝鲜战场与美军飞机的周旋、曾祖父逃荒到苏州的谋生经历、家族中的司机们严格遵守的规矩,都成了小说里最动人的细节。

新书发布会现场。人民文学出版社供图
乱世里的生存从不是英雄叙事,而是普通人在绝境中抓住的那一点点“微光”。毕飞宇作为同行,被这份“微光”打动。很多作家会把这样的题材写成大史诗,可路内没有。在毕飞宇看来,这种克制的表达恰恰是《山水》的高明之处。
好的小说不抒情,而是把情感藏在细节里。路承宗为保护周爱玲,提着刀闯日本军事区。这种藏在行动里的爱,比直白的告白更有力量。“这种写法帮助读者理解生活,看到人性中的善良。路内选择不写他们如何表白、如何结婚,这种省略需要勇气,需要手很狠,但写得特别好。”毕飞宇说。
路内曾在采访中表示:“这部小说谈不上家族叙事,甚至有点‘反家族’。”小说开篇,路承宗就忙着帮孩子们找亲生父亲,而这个拼凑起来的家,却比许多血缘家庭更有凝聚力。“我舅公退休后回农村,门口突然多了个弃婴,警察让他收养,说‘你对领养的儿子好,别人才放心把孩子交给你’。”“家”,不是血缘,而是彼此的选择与担当。
小说中,路承宗对孩子们说:“做你们的爸爸比做司机还难,而且不会有退休的时候。”周爱玲对女儿说:“一辈子,找条回家的路,走很久,看见你自己站在前面。”这样朴素的语言,道出了非血缘家庭中更为纯粹的情感联结。
毕飞宇特别欣赏路内对家庭伦理的刻画:“路承宗临终前为养女争取婚姻认可的段落,展现了非血缘家庭中的深沉情感。这种不抒情却充满力量的处理方式,正是好小说的特质。”
每个人一生都在找寻一条回家的路,但这条路的尽头,其实是与自我的相遇。路内曾在采访中提到,以“山水”为名,寓意深刻:“山水大概有两层意思,一是指人生路,起起伏伏的;二是在小说里特为谈到了,‘看山水’是一种态度,既是胸怀远大,也是隐忍克制。”
“我写长篇有个奇怪的能力,能估算出写完需要多久。《雾行者》算的是5年,40多万字,真的写了4年半;《山水》构思了10年,最后用14个月写完,连除夕夜都在赶结尾。”路内提到,写长篇就像“看得见500米外的宝塔尖”,知道方向就不会迷茫。而这份对写作的认真,其实也源自家族的传承。祖父开车时对轮胎的敬畏,成为他写小说时对文字的敬畏。
谈到自己的写作态度时,路内说:“我是一个比较认真的作家。我到炫技的时候,会稍微提醒一下自己不要这么干,我到特别真诚的时候,也会稍微提醒一下自己不要这么干。你用自己的真诚非要去赚取读者的感情投入,其实也是有一点点问题的。”他认为,作家写小说时需要“稍微冷一点点,往后退一点点,不要替读者先哭”。





 京公网安备 11010102004843号
京公网安备 11010102004843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