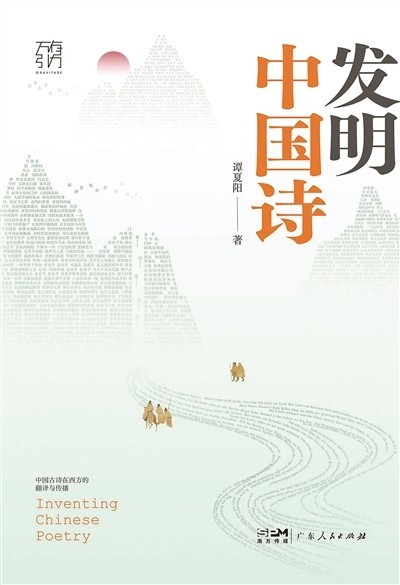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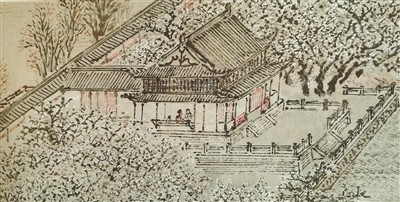
◎邓安庆
2025年诺贝尔文学奖归属匈牙利作家克拉斯诺霍尔卡伊?拉斯洛,这本只是文学界关注的事情,但很快其另一重身份引起了中国大众的兴趣:他是一位资深的“中国迷”。著名翻译家,同时也是拉斯洛多年好友的余泽民曾在《拉斯洛:迷恋中国文化的匈牙利作家》一文中提及,1991年,拉斯洛以记者身份造访中国,这片土地自此在他心中种下痴迷的种子,他盛赞中国是“世界上仅存的人文博物馆”。他不仅是在嘴上说说,现实生活中也身体力行,余泽民文中写到他不仅力促全家人改用筷子吃饭,更走到哪儿都不忘搜集中国相关书籍、关注中国动态;在外偏爱中餐,在家常听京剧,与人交谈时总会不自觉地提及中国。他对古代中国尤为倾心,潜心研读《道德经》,更对李白推崇备至,直言“李白是他最喜爱的中国诗人”。1998年夏天,余泽民还曾陪同拉斯洛沿着李白的足迹漫游,拉斯洛坦言:“我喜欢他的豪放,我喜欢他谈醉酒,谈月亮,谈生活,谈分离,谈朋友——我喜欢他的律动,他无尽的能量,他流浪的心性——我喜欢李白,喜欢这个人。当然,我只能在译文的基础上揣测诗歌,但是揣测的结果总是告诉我,天哪,这该是多么美妙的诗歌。”
为何是“发明”中国诗,而非“发现”?
“我只能在译文的基础上揣测诗歌”,拉斯洛的这句话勾起了我的好奇心。我们都知道,尽管他曾数次踏足中国,却并未掌握中文(对很多外国人来讲,中文是一门多么难掌握的语言)。那么,他究竟是通过哪位译者的译文,接触到李白的诗歌?这些跨越语言的转译,是否真正贴合了李白原作?当李白的诗行被译成其他语言,是不可避免地耗损了原作的精髓,还是在文化碰撞中意外增添了新的魅力?这无疑是一条极具探索价值的线索。顺着这份好奇追索下去,便会自然而然地踏入中国古诗在西方的译介与传播之路。而谭夏阳所著的《发明中国诗》,恰是解开这些疑问的一把钥匙。该书以清晰的脉络梳理了中国古诗走向西方的百年历程,它不仅深刻影响了西方文学的发展轨迹,更成功俘获了一众西方文化精英的心。此时我们便会发现,拉斯洛对中国文化的痴迷并非孤例——在他之前,亚当?扎加耶夫斯基、埃兹拉?庞德、查尔斯?赖特等一众文学巨匠,早已是中国古诗的忠实拥趸,共同促成了中西跨文化传播。
为何是“发明”中国诗,而非“发现”?按理说,西方读者通过译介接触中国诗、感知中国文化,用“发现”似乎更贴合“初识”的本义。毕竟这些诗歌早已在中国的历史长河中存在,本就是被“找到”而非“创造”。但文化交流与传播的奇妙之处,恰恰在于这份“非机械复刻”的转化:接收方必然会因语言隔阂、文化语境、社会国情的差异,无法原样接纳外来文化,反而会在理解、转译与吸收的过程中,赋予其新的阐释与生命力,最终将其融入本国的文学传统。如此看来,“发现”只是跨文化传播的起点——是西方世界与中国诗的初次邂逅;而当这些诗行通过翻译进入译入语系,与西方的诗学理念产生碰撞、关联与化学反应,完成从“异域文本”到“本土可读、可感、可借鉴的文学资源”的蜕变时,便抵达了“发明”的境界。作者在序言中也点明了书名的由来,正是源于艾略特评价庞德的那句名言:“庞德是我们时代中国诗的发明者。”
反过来看,国外文学作品传入中国的历程,不也正循着这样的逻辑展开?它们必然要历经一番“在地化”的调适:从语言符号的转译到文化内涵的适配,从最初的生硬模仿到后来的汲取养分、自主创作。我们对这些外来文学的接纳与转化,从被动接受到主动融合,最终催生出属于中国文学的崭新表达,这何尝不是另一种意义上的“发明”?熟悉中国现代文学史的读者或许知晓,20世纪30年代,鲁迅便曾围绕直译与意译、翻译优先级、译文风格等议题,与梁实秋、赵景深、瞿秋白等人展开过激烈论争。他提出“硬译”(一种极致化的直译)理念,却也并非拘泥一端,而是会根据文本类型灵活选用意译,其辩证的翻译思想至今仍具启发。
迥异的翻译观念与实践路径
而在西方世界,围绕中国古诗的译介,类似的理念碰撞同样上演。不同时期的西方译者,基于自身对中国诗的认知深度与西方读者的接受需求,形成了迥异的翻译观念与实践路径。书中记载的一则案例尤为耐人寻味:19世纪中后期,中国古诗在西方的译介尚处懵懂起步阶段,彼时的译者虽对中国文化满怀好奇,却缺乏足够深入的了解,翻译中难免出现“自由发挥”的情形。譬如王昌龄的《闺怨》:“闺中少妇不知愁,春日凝妆上翠楼。忽见陌头杨柳色,悔教夫婿觅封侯。”法国译者戈谢将其编译成《西窗》:“率领成千狂怒的战士,在铜锣的怒吼声中,我的丈夫出发奔向光荣/我开始为获得少女的自由而高兴/现在我隔窗望着柳树那发黄的叶子,他出发时,它们还是嫩绿的/他是不是也一样为离开我而高兴呢?”原诗的闺怨之愁与译诗的直白揣测可谓南辕北辙,读来令人忍俊不禁。
步入20世纪,随着西方世界对中国文化的认知逐渐深化,“如何翻译中国古诗”成为值得深入探讨的议题。前文提及的庞德,之所以被艾略特誉为“我们时代中国诗的发明者”,正是因为他并未执着于译文的逐字精准,而是主张对中国诗进行创造性转化,使其契合意象派的艺术理念。1915年,他的《神州集》问世,即便存在不少改译之处,却为英语诗歌注入了全新的句法结构与表达可能。他也没有刻意回避译诗改写的问题,“至于改写,我们可以发现所有的绘画大师都向他们的学生建议以临摹名画作为开始,由此走向自己的创作。”但作为庞德的好友,阿瑟?韦利却秉持着截然不同的翻译观。他认为,译者不应试图替代原作者,“因为他的使命是向读者阐释、传达原作者的意义,而不是进行‘再创造’。”他们的分歧,代表了两种不同的翻译理念,也是很多译者争论不休的焦点。
以独特的魅力影响西方诗歌发展
“由此走向自己的创作”,庞德所言不虚。诚如作者在前言所述:“中国诗在西方译介与传播的过程中,也以其独特的魅力影响着西方诗歌的发展。两次美国现代主义诗歌运动,都与中国诗有着莫大关系。两次运动促使美国诗歌走向现代化和民族化,最终摆脱‘英国附庸’,创造出独具美国本土化的全新诗歌,在诗歌史上具有深远意义。”第一次浪潮出现在20世纪一二十年代的美国现代主义诗歌运动中,意象派是其核心力量。该流派“主张把诗人的感触和情绪全部隐藏到具体的意象背后,即只描写具体的对象,而不去探寻事物之间的本质联系与阐发的社会意义”。这恰恰是中国古典诗歌的典型特质,故而备受意象派诗人推崇,他们纷纷对中国诗歌展开大量仿写。第二次则发生于20世纪五六十年代,这场被称为“旧金山文艺复兴运动”的诗歌浪潮,先后催生了垮掉派、深度意象派等诗歌流派,它们与中国诗歌同样渊源深厚,“与第一次关注中国诗句法和意象不同,本次‘中国式’诗人更加倾心中国诗所蕴含的‘禅’与‘道’,也即是说,他们更希望深入到中国美学的核心中去,以期找到治愈精神创伤的良药。”
除了这两大代表性流派,更有众多深受中国诗歌浸润的西方诗人,他们以散落却呼应的创作,共同构筑起一个隐形而庞大的文学体系。由此不难看出,中国古代诗歌的跨洋引介对西方文学产生的深远影响,其力度与广度,绝不亚于西方文学对中国现当代文学的辐射。一个颇值得玩味的对比是:若问中国当代诸多作家,哪些作家曾影响过他们的创作,想必多数人会信手拈来一串西方经典作家的名字,反观中国古典文学,却往往知之甚少。即便同操汉字,古典文学还是有理解门槛的;而那些经翻译转译的西方作品,反倒因语言的当代转化,让人能轻易进入。反观西方作家,正如作者所指出的:“在他们眼中,中国古代诗歌与现代诗歌,甚至是当代诗歌,没有本质上的差异,因为区别最明显的文本形式、韵律节奏都在翻译之时被无形地抹掉了。在某种程度上,这些经过翻译的古典诗歌比欧洲的现代诗歌还要优秀,可以作为他们写作参照的一个典范。”这一现象恰恰印证:无论是西方文学之于中国写作者,还是中国古代诗歌之于西方创作者,本质上都是可供汲取养分的文学资源。而翻译不可替代的重要性,在此刻愈发清晰可辨。可以想见,像拉斯洛这样醉心于中国文化的“中国迷”,还会在未来不断涌现。而这条东西方文学相互启迪、彼此“发明”的道路,也会不断向更遥远的未来延伸。





 京公网安备 11010102004843号
京公网安备 11010102004843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