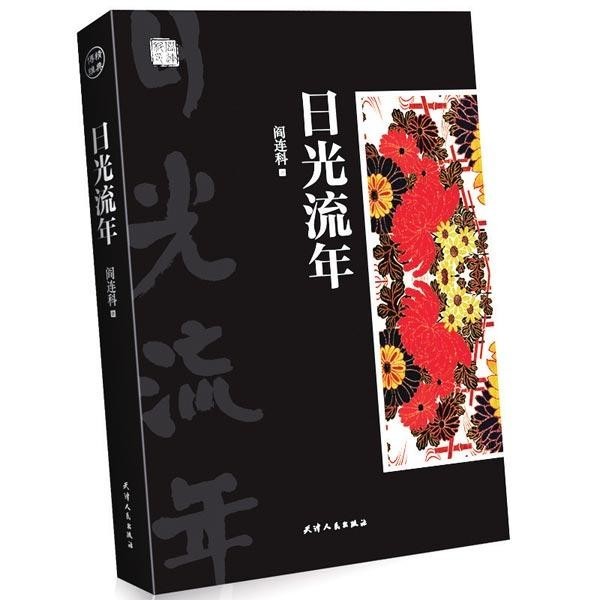
近几年读过的小说中,阎连科的《日光流年》是让我印象非常深刻的一部。
不得不承认,我从未读到过一部如此密集地谈论死亡的文学作品。一开始,我本能地拒绝这样的题材,因为太过压抑,人生本来已经够辛苦了,我总是想去选择一些相对轻松的作品来阅读。但没有想到的是,读完这部小说之后,我对它有了截然不同的认识。
《日光流年》开篇的第一句话,就是“嘭的一声,司马蓝要死了”。小说写了三姓村的村民在司马蓝的带领下,几代人都锲而不舍地寻找着长寿的方法。他们试过数不清的办法,包括引水、换土,就是为了找到村里人活不到40岁就会死去的原因,从而破除这个魔咒。但所有艰苦卓绝的努力都以失败告终。
有关命运的无情和无从反抗的主题让我想到了古希腊神话中关于俄狄浦斯王的故事。俄狄浦斯王为了反抗自己“杀父娶母”的命运,作出了各种尝试,但最终却恰恰杀死了自己的父亲,娶了自己的母亲。人在命运面前是何其渺小!三姓村的人在打破命运魔咒上付出的努力无疑也是徒劳的。
但恰恰是因为这种努力的徒劳,才真正彰显出它的弥足珍贵。司马蓝没有因为一次次付出巨大代价尝试的失败而放弃努力,相反,每一次的失败都不能阻止他产生新的希望。世间有什么事物比希望更具有力量,更令人动容呢?在某种意义上来说,《日光流年》并不是关于三姓村的人的离奇故事,而是关于整个人类的寓言。三姓村的人不到40岁就会死,这看似离奇,却又并不离奇。在现实世界,人的寿命同样有限,到了那个限度,同样会死。三姓村的境遇只是把人类的普遍境遇推到了一个极端化的情境。自古以来,渴望长寿就是人类的重要追求,君王将相如此,普通人亦然。但自然的规律何尝由得人反抗?
在这个意义上,三姓村的人对待死亡的态度却令人称奇:他们把死亡视为一件非常稀松平常的事情。在这里,“死就像日出日落,刮风下雨一样寻常而又普遍”,司马蓝三兄弟讨论各自坟地的面积就像普通人在买菜时讨价还价一样波澜不惊。也许阎连科想要探讨的问题之一,就是人们应该如何面对死亡。每个人都应该像“司马蓝们”一样,学会与对死亡的恐惧共存,甚至通过战胜这种恐惧来完成自己的成人仪式。
而相比对死亡问题的探讨,《日光流年》更打动我的是阎连科对生命的书写,写那些在死亡的阴影下,仍然不停流转的、美好的生命。或许,正是因为存在着无可逃避的死亡和无法脱离的苦难,生命中的那些口角、琐碎、或大或小的梦想才显得弥足珍贵。司马蓝的一生都在和三姓村的诅咒做抗争,他的行动表面看起来是悲剧性的,因为他从未成功过,但在这些抗争的缝隙里,他却爱过,也被爱过。他和杜竹翠的婚姻没有爱,但他和蓝四十虽然没有婚姻之实,却终生相爱。这份爱真真实实地存在过,深情而缱绻,哪怕肉体的消亡也无法将其磨灭。
他还拥有过真正的希望,这希望带给他和他的村民无限的憧憬。早在他的爷爷司马南山那时,村里的人们就通过卖人皮的方法换来了大笔的钱。司马南山幻想着要用这笔钱买10头毛驴,开两个染坊,然后用这些毛驴从青岛驮盐回来,也许就能让村里人活到50岁、60岁、70岁,乃至80岁。这美好的愿景让他忘记了腿上刚刚被割掉皮的剧痛。可3个月后,他的希望就破灭了。然而阎连科没有去刻画村人的失望,反而这样写道:“可终归,那是一次发财的冤皮生意呢。”也许,希望的真正意义并非在于它是否能够实现,而恰恰在于它的存在本身。希望的存在就是最重要的,因为它照亮了原本绝望而黑暗的生活。
《日光流年》在结构上的独具匠心是另一处让我叹为观止的地方。阎连科没有像通常的写作顺序一样,从一个人的出生开始一直写到他的死亡,而是反过来,从司马蓝的死亡开始,写到他的出生。在小说结束的时候,阎连科写到司马蓝的母亲在一群人的围绕下生下司马蓝:“司马蓝就在如茶水般的子宫里,银针落地样微脆微亮地笑了笑,然后便把头脸伸送到了这个世界上。”在读者们看完了司马蓝一生艰苦卓绝的努力之后,世界重回清明,司马蓝变回子宫里的胎儿,正要降生到人间。生无疑是死最好的平衡,人类的生生不息既是对死亡的补偿,也是对死亡的安慰,二者互为因果、互为条件。小说的结构由此完美地反映出了这一形而上的思辨,实现了形式与内容的高度融合。
所以我想,阎连科在《日光流年》中所要强调的终归不是“死”的阴霾,而是要凸显“生”的奇迹。英国作家石黑一雄曾经说过,人在努力的时候,往往看不到事情的全貌,无法预知自己的努力是否会获得自己渴望的结果。但正是因为这样,人在面对绝望时仍然保持尊严,仍然付出艰苦卓绝的努力,这是何等的令人动容。从某种意义上来说,《日光流年》处理的正是同样的主题。小说以表面上的荒诞反映了命运的无法参透,以及人在自然面前是多么渺小。但更重要的是,虽然人的努力可能是盲目的,甚至是徒劳的,但人类祖祖辈辈前赴后继不断尝试,满怀着对生命、对同类强烈而真挚的热爱,以及对未来永不磨灭的希望,却是如此的荡气回肠。这也是这部小说不仅给予我们启发,还给予了我们莫大精神力量的原因。





 京公网安备 11010102004843号
京公网安备 11010102004843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