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思想与文学间遨游
发稿时间:2024-01-01 14:44:00 来源: 光明网-《光明日报》
【读书者说】
作者:陶慧(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讲师)
何谓为文?
《左传》曰:“太上有立德,其次有立功,其次有立言。虽久不废,此之谓不朽。”在这一为中国古代士人所熟知和信奉的思想体系中,文学写作,往往被归之于“立言”范畴,即通过文字著述,表达自身的思想观念,实现个人的社会价值。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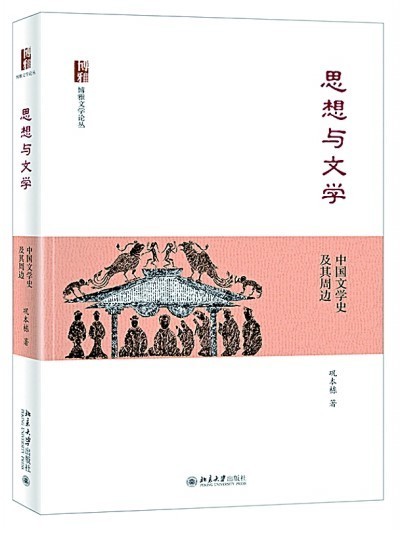
《思想与文学:中国文学史及其周边》 巩本栋 著 北京大学出版社
虽然“立言”的社会价值似乎不及“立德”与“立功”,但对于中国古代士人而言,其追求个人主体价值实现的思想内核却是一致的。于是,作为“立言”之重要一途的文学写作,或意在言志寄情、申纾性灵,或追求经纬天地、匡主和民,总难免与重道修身、经世致用等观念交织相融,同构于中国古代包容万象的思想文化体系中。因此,研究中国文学史,向来无法脱离对相关时代文化背景的阐述。
然而作为历史文化图景的重要组成部分,文学自身具有十分复杂的内部情况,政治、经济、学术、宗教等其他思想文化资源,对不同创作主体的影响程度也不尽相同,如果只是泛泛而谈,则很难真正把握文学发展的深层历史脉络。对于这一点,南京大学文学院教授巩本栋的《思想与文学:中国文学史及其周边》一书,在方法论层面或可给予我们有益启示。
全书时间跨度纵历先秦至明清,但并不像一般的文学史著作那样追求面面俱到,而是选取每一时期若干重要文学个案,站在思想文化的宏观视角,采用考据与批评相结合的研究方法,于纷繁复杂的时代背景中,抽绎出影响文学发展最关键、最直接的外部要素,为中国古典文学研究开拓了新的思想文化视域。
文学与修身
关于文学与个人德行修养、志趣观念之间的关系,《尚书·尧典》中已有“诗言志”之说,《毛诗序》更进而论之:“诗者,志之所之也,在心为志,发言为诗,情动于中而形于言。”此“志”,一般理解为作者的思想、情志、抱负等,在某种程度上亦可视为作者个人品格操守的文本外化形态。

《西江月·黄州中秋》 洪健 绘 图片选自中译出版社《画说宋词》
如中国最早的长篇政治抒情诗《离骚》,即可视为屈原之“志”的体现。诗中所写“屈心而抑志兮,忍尤而攘诟”“抑志而弭节兮,神高驰之邈邈”,既包涵了屈原的政治追求,也表明了他一直所坚守的清白高洁、刚正不阿的个人品行,以及固守正道却遭谗见疏的忧愤。
对于这篇在先秦文学史上占有举足轻重地位的作品,无论其内容主旨、艺术风貌,还是作者的思想情感、创作动机等,历代论者解读已多。巩本栋先生则另辟蹊径,在本书中着重辨析屈原个人情怀寄托的曲折变化过程。通过对《离骚》的文本细读,巩本栋发现其思想艺术有一个十分鲜明的特点,即前半部分悲愤嗟怨,“流露出对楚国前途与命运的深广的忧患意识和责任感”,具有偏重现实的创作倾向;后半部分则结想宏富,“反映出诗人高远的政治理想追求以及卓异不凡的才情”,即浪漫瑰丽的创作特色。至于转变的肯綮,正在于诗中极为关键的两句——“退将复修吾初服”与“就重华而陈词”。前者是诗人现实境遇中理想的失落,通过内转式的自我疏解,寻求摆脱心理困境的力量,最终选择坚守正直的品格;后者则结合历史做出想象,转而向外,向先王前修寻求支持,坚定“吾将上下而求索”的决心。于是,热烈无羁的浪漫想象与忠直坚定的人格情操完满地融为一个有机整体,并且“开创了中国抒情诗的真正光辉的起点和无可比拟的典范”。
值得注意的是,屈原选择的“退修初服”与“陈词重华”两条精神路径,不仅关乎他个人的品格,而且具有强烈的现实意义和深层文化心理背景。如前者的核心在于“修身”,而先秦诸子虽在学术观念上百家争鸣,但无论老、庄还是孔、墨、孟、荀,对修身却无不重视,实为先秦士人共同追求的品格。后者的要义在于推尊先王,此又为以儒家、道家为代表的先秦诸子的普遍观念。由此可知,这两种思想倾向不仅是屈原的个人选择,同时深含着先秦士人“以道自任、注重自身修养的思想文化底蕴”,铭刻着国家治乱、社会沉浮的历史殷鉴对诗人深重的心理影响。于是,这种体现于文学作品中的修身言志之意,便也带上了时代精神所赋予的心理积淀与文化态势。
文学与治学
《礼记·大学》云:“欲诚其意者,先致其知”。作为正心、诚意、修身的前提条件,中国古代士人对于致知、治学的追求,既与个体道德修养有关,又有显著的“立言”意味,在心理动因方面与文学创作具有一致性。
因此,士大夫文人的学术思想,往往会对其文学写作产生影响。这一点,在注重文治的宋代体现得尤为明显。宋代士人学识渊博,格局宏大,正如王水照先生所说,多为“集官僚、文士、学者三位于一身的复合型人才”,论者亦每谓宋人好“以学问为诗”,因此要研究宋代文学,不可不关注宋人的思想学术。
在《思想与文学:中国文学史及其周边》一书中,有《欧阳修的经学与文学》《苏轼的思想学术与文学创作》,也有《南宋文化“绍兴”与〈宋文鉴〉的编纂》等,其关注重点正在于此。其中,尤以第十一章论欧阳修的思想学术与文学之关系最为典型。
欧阳修在经学、史学、金石学等学术领域皆有成就,经学之中,尤深于《易》《诗》《春秋》。作为北宋开一代风气之先的文士领袖,欧阳修治经学最大的特点,便是以人情常理为本,对经义本身进行解读。至于前代儒生奉为圭臬的传注,欧阳修则大胆怀疑,对北宋疑经风气的形成产生了重要影响。至于其思想渊源,巩先生通过考察欧阳修的生平家世与治学经历,指出这种无所束缚的学术主张,乃是由于其家世贫寒,少无所师,故不必如汉儒经师一般固守师承家法,而能够学出己见,大胆怀疑。这一点,又正与北宋士人多出于庶族的时代背景有直接关系。
可以说,欧阳修的治学经历与学术思想,为我们理解疑经风气何以会在北宋出现提供了例证。而对于研究他的文学创作,同样具有重要意义。关于经学与文学之间的关系,欧阳修曾大胆提出“六经皆文”的主张:“言以载事,而文以饰言。事信言文,乃能表见于后世。《诗》《书》《易》《春秋》,皆善载事而尤文者,故其传尤远。”在破除了对传注的迷信后,将六经视为出自圣人之手的天下至文,盛赞其“事信言文”,从文章学的角度对儒家经典进行观照。于是,欧阳修的文章写作风格往往自觉向六经靠拢,尤重《春秋》,追求言简意赅、简而有力的笔法,以及平易畅达的艺术风格。这既是欧阳修个人文学创作的基本风貌,也是由他所积极倡导的北宋古文运动的审美追求,究其根柢,正是对先秦儒家经典在文本层面的复归。要解读以欧阳修为代表的北宋古文风格的形成,不应忽视其中深刻的思想学术意义。
文学与经世
对于古代士大夫来说,通过建立事功实现经世济民的理想,往往是最普遍的追求,也是实现个人价值的最直接途径。而文学,既在政治功用方面被认为具有“上所以敷德教于下,下所以达情志于上,大则经纬天地,作训垂范,次则风谣歌颂,匡主和民”(《隋书·文学传序》)的作用,自然而然也与文人经世思想有千丝万缕的联系。
而“文”与“用”的关系,也是《思想与文学:中国文学史及其周边》一书的论述重点,其中,尤对北宋时期观照最多。
北宋的变法与反复,本为革弊图新与因循守旧两种不同政风、士风之间的矛盾,无论是否主张革新变法,其出发点皆为国计民生,本意在于解决北宋迫在眉睫的社会危机。然而随着形势的发展,变法意味逐渐改变,意气之争、政治倾轧等因素也进入其间。对于节操高尚、以天下为己任的文士来说,如何在波诡云谲的政治风浪中坚守自己的理想,此过程中,文学又扮演着怎样的角色,是值得深入探究的问题。
对此,中国文学史公认的大家苏轼可作为观照对象。在书中,巩本栋先生通过对苏轼屡次遭贬所涉历史文献与文学文本的细致梳理,深入分析了的苏轼的政治理想。若以北宋律令论,苏轼或确有“作匿名文字,谤讪朝政及中外臣僚”之罪状。然而若结合中国古代诗歌“兴观群怨”的功能来看,诗歌本有反映现实、补察时政以“风谣歌颂,匡主和民”的传统。苏轼写作一系列相关诗歌,正有“作为诗文,寓物托讽,庶几流传上达”的意味。再联系北宋政坛渊源有自的“不杀士大夫及上书言事者”的传统,“乌台诗案”实为一桩冤案。隐藏在那些讽谏诗歌文本背后的,是一位士大夫饱含的对下层百姓困苦生活的同情,也蕴有其自身矛盾复杂的心态。
作为中国古代思想文化图景的重要组成部分,文学史的发展从来不是孤立的,围绕在其周边的思想资源,也并非单纯以“背景”的形式存在,而是与文学自身的发展脉络彼此交织相融,共同形成文化发展、文明推进的合力。
这便要求我们在进行文学史研究时,不能脱离宏观的思想文化视域。然而具体到文学史本身,正如巩本栋先生所说:“在众多的思想文化背景和因素中,总有一些最直接、最重要的背景因素在起作用,而另一些因素则相对影响较小。”那么,要如何揭示出那些最本质、最直接、最具决定性的因素,以对文学发展的来龙去脉有更加清晰的把握,同样是文学史研究需要不断思考的问题。而这一点,也是巩先生此书给予我们的重要启发。





 京公网安备 11010102004843号
京公网安备 11010102004843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