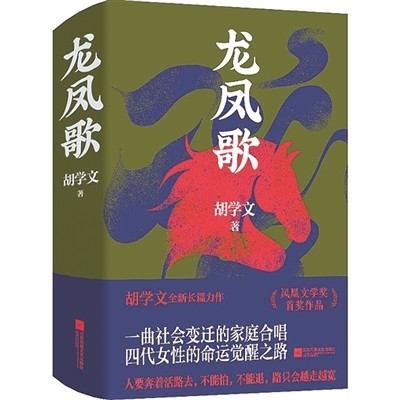
多年写作,每有闪念,我会马上记下,身边有纸笔当然好,没有便记在手机上,再转记到纸上。我有一种强烈的感觉,文字到了纸上,就如种子植入大地,不但可以生根,还会按照自己希望的方式生长,且无需担心被窃。不是什么秘密,习惯而已。之所以说是闪念,因为常常来得极快极突然,有时持续久一些,有时稍纵即逝。清早急步,旅行途中,酒酣之际,半夜梦醒,读书期间,被某种情绪浸没时,没有确定的节点,可遇而不可求。也许这就是所谓的灵感,但我不敢这么定义。奇妙的灵感应属于博尔赫斯、卡尔维诺这样的世界级大师。于我,称为写作的种子更为恰当。所谓种子,形状各异,一个词、一句话、一个故事、一个人物、一段梦境,而记述有繁有简。并非所有的种子都发芽,有一些在彼时兴奋不已,但一年或数年之后,就演变成石子,暗淡无光。另一些,被他者“捷足先登”,发现有作家写过类似作品,写作的劲就不足了。勉强写出,或有抄袭之嫌。从另一个角度说,若别的作家也能想到,那就算不上是奇思妙想。这样的种子最终会被抛弃。
我有一个专用记述闪念或种子的笔记本,密密麻麻,几近杂乱。里面的多半种子都生根发芽了,有长篇,如《有生》,有中短篇,如《从正午开始的黄昏》《风止步》《龙门》《奔跑的月光》《三月的秋天》等。即便发芽,也不是一蹴而就,种子生长得极为缓慢,特别是长篇。其过程是先由纸入脑,再由脑入心。入脑阶段,小说的题目、叙述方式、视角、人物(包括名字、性格、彼此关系)、结尾等大致有谱了,“万事俱备只欠东风”,这“东风”便是激情和动力,有它们才能由脑入心。也可以说,一旦入心,便有了写作的冲动。部分情节和细节也是揣于心间的,而相当一部分,特别是细节,则是在写作过程中临时产生的。这也是写作的乐趣之一,常有意外收获。原本是冲某个方向去的,可中途失控,拐往另一方向,亦奇亦险,却是惊喜不断。我的一位作家朋友,写至得意处,必定要搞二两小酒,搞个小小的个人狂欢;另一位朋友,半夜打电话给朋友,只因太兴奋了,难以自控。如果不从事写作,是很难理解的。我当然能体会,且常生羡慕。不过我对这喜悦常常是独享。小说没收尾,不谈论,更不示人。被“窥见”,很可能兴奋不再,写作的动力就没那么足了。有些长篇,前面很好,后面明显感觉气力不足,我想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写到后来,作者激情丧失,气泄掉了。有激情,作品未必有光,但若没激情,肯定写不好。我说到入心,就是这个缘故。
《龙凤歌》(江苏凤凰文艺出版社)与我以往的小说不同,那枚种子没有经过由纸而脑的环节,而是直落心间。写作的过程如同怀胎,从这个意义上讲,是直接怀上的,而且孕期很久。我清楚地记得那是2011年隆冬,一个冷得不能再冷的日子。我已年过不惑,生活、写作大抵是坦顺的,至于风风雨雨,谁不遭受呢,那是人生的一部分。于作家而言,遍尝酸甜苦辣,才能写出生活的滋味。但在那个滴水成冰的日子,我遭受重击,也可以说,被狠狠捅了一刀,疼痛得难以形容。之前的跌倒、陷入泥沼,不过是皮毛。也是在那一刻,我悄然止步,回望来路,思考命运。
作为写作者,其实每次创作都是思索之旅,笔下的角色不同,命运各异,虽然多为虚构,但就倾注的情感与精力而言,每个角色都和自己有着密切的关系,甚至是“血缘关系”,哪怕不喜欢的人物。他们成为这样或那样的人,大致轨迹可寻。寻见,写出其背后的必然和偶然,小说即成。所谓的“寻”,其实是“思”的过程。我以为自己思考得够深了,待痛而回首,才意识到之前的思考是站在外部的。内部与外部的感觉完全不同。写不同的角色,我会把自己变成那个人,但就如演员,演技再好,终究是演。先前的写作,某种程度上也是演,进得去还要出得来,有一定的时间性。而立于内部,我不需要演,也没法演。我被迫成为角色,没有任何选择的余地,没有丝毫逃遁的可能。我只能是我,必须面对人生的残酷、锋利、无常。
彼时,我并不知道一枚种子植于心田,我将写出一部因情而生的作品。意识到“受孕”是后来了。说实话,这并不是我想要的,更不是我计划的,如果可以选择,如果能避开那一刀,我绝对会舍弃这部小说。但我不能选,既然“怀”上,就“生”下来,这是我能做的,也是必须要做的。
何时“分娩”?我不知道。就像哪吒的母亲殷夫人并不清楚她怀胎三年六个月后才生下哪吒一样,我亦不能推算。我能做的就是等待。那时,我刚开始《有生》的写作,以为《有生》杀青,怎么也可以“生”了,事实是并没有,虽然我该准备的都准备了。就像许多母亲那样,婴儿衣服都做几套了。倒是不急,时常感觉到“胎动”,倒也甜蜜。
2021年春夏之交,工作调动,我迁至南京生活。已“孕”十年,尚无“生产”迹象,我以为还要许多年。我构思了一部长篇,案头工作等着我,费时,也需专心。
2022年伊始的一天,晨起,因天气缘故,我未能如往常一样下楼快走,便坐于桌前,凝望雪雨飘落。天色尚暗,屋内昏昏。我如一个迷途者,难辨方向,只是没有迷路的慌乱。脑无杂念,心静如水,那是一种与茫茫大地融为一体、突然接通了什么的感觉。疼痛突至,仿佛即将“分娩”的讯号,我既惊又喜。以为还要数年,没想到突如其来。那就“生”吧,与此同时,小说的第一句话也浮于脑海。首句关乎叙述方式,也关乎叙述腔调,因而至关重要,完全凭感觉、靠气息。在此之前我没想过,可以说,这是另一重惊喜。我说过,这是一部为情而生的小说,我没想那么多,只想让它“呱呱坠地”。
但铺开稿纸,我不得不进行思考或者说探寻。没错,我是为情而作,不必硬性地、牵强地将某些人尽皆知的“意义”“主题”充塞于字里行间。可我写的终究是小说,不是生活的展览,不能任凭故事的洪水汹涌席卷一切。我得让她和他,让她们和他们立于波涛之上,我要追寻人物的人生轨迹,破解命运的谜题。我能看清他(她)们,能看到他(她)们站在起点,达至终点的样子,但其行进的路,于我是模糊、费解的,而追寻和破译,也是激情的一部分或动力所在。
我想到了几个词,文化、时代、环境、性格、基因,以及难以用语言定义的神秘和奇诡,它们如何合谋、如何分工、如何协作,让一个人成为这样而不是那样,人物又是如何与它们有意识无意识地较量的?从某个角度讲,小说呈现的是破译、破解过程。上述词汇,不过是确定大致方向。
作品完成,作家应该消隐,尤其于文本的解读,是不该多言的。关于其他,倒是可以多谈。比如写作准备和写作习惯。有人夜半,有人晨起,我基本是下午写作。写《龙凤歌》时,有几个月是凌晨加午后。每日写作时间久,即便精力跟得上,激情也难以持续,所以写了一段,就回到之前的习惯。而那一个个从夜色初褪至艳阳高照的日子,独坐桌前,神游天地,回忆起来倒也甜蜜。
一位作家朋友讲,有了开头的一句话,就可以落笔,不考虑其他。技术在身,有信心有雄心,当然没问题。我难以如此,需要很多准备,尤其是长篇。即使《龙凤歌》这样如同血肉的小说也是,甚至还要给人物写一个简单的小传。窃以为,长篇小说在相当程度上是结构的艺术,结构有隐有显,像略萨的《绿房子》《公羊的节日》偏于显性,福楼拜的《包法利夫人》偏于隐性,命运即结构。两者没有高下之分,不过是艺术追求的区别。
小说的题目很重要,特别、响亮、有味道,可为小说增色。我不是特别会给小说起名字,相当一部分作品是刊物编辑、主编改换的。如中篇《背叛》《苦水淖》《飞翔的女人》,皆为《人民文学》改定,《跳鲤》《龙门》则是《花城》改的。《有生》初始题目是《生死镜》,发给《钟山》时改为《万物生》,主编贾梦玮认为不妥,列了《有生》《天地大德》两个题目让我选,我选了《有生》。他回说也中意这个,算是不谋而合。回首再看,《有生》确实是最合适的。《龙凤歌》原来的题目是《龙凤图》,贾梦玮认为图字缺少动感,遂将“图”改为“歌”。
写作是冒险的旅程,沉于其中,多觉其喜其乐,完成后却是不安的。《有生》发于贾梦玮信箱,我的心基本半悬着,春节期间,收到他的信息,说刚看了几十页,但感觉这是一部大著,嘱我先不要给他人看。贾梦玮办刊多年,个人也写作,眼光独具,他如此言,我当然欣喜。《龙凤歌》也是先发给他的,他没用“大作”冠之,回言“特别”,这正是我期待的,相信这也是每一个作家的愿望,每部都与上部有所不同。如果要我言说已近花甲之龄的梦想,那就是数年之后,再产一个特别的孩子。
(作者系江苏省作协副主席、鲁迅文学奖获得者)





 京公网安备 11010102004843号
京公网安备 11010102004843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