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宝树 受访者供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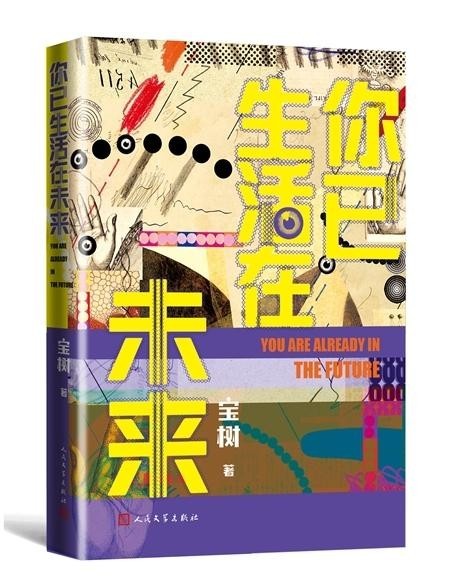
《你已生活在未来》书封 人民文学出版社供图
在北京大学,当时22岁的宝树写好了一部科幻小说的结尾——3000字的结尾,他自认为堪称全文最绝妙的反转;但直到8年后,在比利时鲁汶大学,这个小说才完成了其他部分。这是宝树2012年发表的第一部科幻小说《关于地球的那些往事》的创作过程。
“记得那天心情低落,但写宇宙非常解压,动辄几百亿光年的宏阔尺度,让人觉得,人类的那些事儿都不是事儿。”宝树说,“如果那天不是偶然翻出这个未完成的稿子,不去写完它,我可能一辈子都不会写科幻小说。”
但最近,宝树新出版的小说集《你已生活在未来》,“尺度”就显得小了很多。发生时间是“不远的未来”,发生地点是“我们的周遭”,连故事桥段都有些家长里短:高考、相亲、结婚、生子……那些科幻小说里的东西,正一步步渗透我们的现实生活。
未来已来。当伦理秩序的标尺不再严谨,当实感与虚拟难以界定,当情感失去时间的承诺,身处其中的我们将变成何种模样?近日,宝树接受了中青报·中青网记者的专访。
中青报·中青网记者:书中故事的发生时间都是“近未来”,数年或者数十年后,是我们这代人还能看见的时代。这个时间段对你的吸引力是什么?
宝树:《我的高考》那个故事的时间设定,是2027年,那是我2013写的小说,当时觉得10多年很遥远,现在已经快到了。故事讲的“聪明药”,当时在国外稍有苗头,现在已经升级迭代,在国内也有露头。当时我写主人公之间还用短信联系,后来出现了微信,所以我在结集出版时作了修订,把短信改成了微信。本来想把时间再往后推10年,但想想还是保持作品本身的原貌更有意义,所以没有改。
科幻是对未来的想象。只是曾经我们想象的未来,可能是遥远的时间之后,是一个与“当下”割裂的地带;但这本书中的未来,是与我们当下的社会经验、科技发明密切相关的,甚至已经在改变我们的生活,比如人工智能、基因测序,在现实中已经有“低配版”的应用了。
在“近未来”,未来与现实的边界已经非常模糊,甚至可以说没什么边界,互相渗透、短兵相接。这个地带有很多模糊的、暧昧的、纠缠的、碰撞的东西,这是这类科幻吸引我的地方。
中青报·中青网记者:遥远的未来,无论好坏,我们都可以远距离观察;迫近的未来,可能与我们直接发生关系,会不会带来不安全感?比如,人工智能。
宝树:是的,我们与人工智能已经不是一个“安全距离”。而且AI发展的速度还会越来越快,现在萌芽的东西,明年也许就铺天盖地;现在流行的东西,明年也许就消失了。科幻的一个永恒主题就是技术失控,以AI为例,都不必幻想AI觉醒后要毁灭人类,它起码已经能替代很多人类的工作,这就够可怕了。
中青报·中青网记者:书中有一个故事是关于AI拍电影,现实中已经出现了AI写作。你会让AI辅助写作吗?
宝树:目前不会。倒不是说我在伦理上、道德上有排斥——当然也有,但创意性的文字,AI无法帮我写。我也实验过,让AI给我写一段,但它生成的都是那种初看高大上,实际上逻辑跳脱、满是bug(漏洞)的东西。小说创作,写每一个人物、每一个细节,都有其目的,AI暂时还无法把握这个意图,除非你输入长长一大段提示词,可能有几句话能用,但我还得整理、组合半天,不如我自己写。在几年之内,AI还无法取代作家。
但我也发现,如果输入一篇小说,让AI分析,出一个书评。它写得还像模像样。
中青报·中青网记者:已经有AI写作的散文发表在报纸上了。
宝树:我也看到过。AI写作的特点,就喜欢用大量的数字和毫无意义的修辞,看似很宏大,实则很浮夸。现在我是一些科幻征文比赛的评委,能看出一些投稿是AI写作的,可能有10%-20%的比例。
但AI会不断进化。5年,或者10年后会什么样,我不知道。到时候,AI也许还能针对不同读者的喜好,生成满足读者期待的文本,你可以选择喜剧或者悲剧结尾,只要付费。
中青报·中青网记者:你也特别关注科技时代人的情感体验?
宝树:如果写科幻纯写技术,那就不是小说了,像一个说明书。其实我们对科技的思考、公众关心的话题,终归是关于人的生活。而生活的很大一部分就是情感人伦,包括爱情、亲情、友情,还有一些奇特而复杂的羁绊。
刚才我说未来与现实已经互相渗透,是一个互相影响、互相牵扯的场域,这时候你会发现,人的情感也处于一个动荡不定的状态。比如,亲人去世了,你可以做一个仿生人;你喜欢哪个明星,也可以定制一个。人类用科技满足自己的欲望与愿望,这些想法都是与情感相关的。科幻与情感密切结合,才会变得有意思。
中青报·中青网记者:但是在科幻背景下,这些情感似乎变得更加危险了?
宝树:是的,这也是技术失控的一种表现。比如,将来人类就想和AI谈恋爱,因为它会对你百依百顺,每句话都说到你心坎上。
中青报·中青网记者:那你会和AI恋爱吗?
宝树:目前不会。我认为爱情的一个关键点不是索取,而是奉献。谈恋爱的时候,你会以对方为重心,会因为对方而改变自己的一些问题。这是一个双方不断磨合的过程,来让爱情达到更高的境界。和AI恋爱可能一开始很舒服,瞬间达到舒适区,但没办法往更深处走。
中青报·中青网记者:你主编过《科幻中的中国历史》,个人作品也常融合历史与科幻元素。“往前看”的历史与“往后看”的科幻,有什么内在的相通之处?
宝树:历史和科幻,写的都是和现实不同的读者比较陌生的世界,是一个异域。用科幻写历史,常见的有时间旅行,即“穿越”;也有“或然历史”——从既定历史的世界中分叉出来的,假如历史不是这样则会怎样,比如郑和舰队发现了美洲会怎样,美国南北战争南方赢了会怎样;还有“错史”,把历史元素用到未来或者全然虚构的时空,比如我写过一本书叫《七国银河》,讲的是银河系里的战国七雄。
历史元素可以用科幻来重构,也可以帮助科幻去想象另一个奇异的时空;科幻能把历史中很多潜藏的东西重新挖掘,在正史之外赋予历史细节更多的意义。
中青报·中青网记者:不久前,北大哲学系主任的开学致辞“出圈”。作为北大哲学系的毕业生,这个学科背景对你的写作有什么影响?
宝树:科幻是一种想象,想象就会超出日常,哲学其实也是超出日常的东西,比如去关心宇宙的起源、人类的本性。只是哲学是用理性探讨的方式去处理这些话题,科幻更多的是想象,但双方是可以互相渗透和转化的。
比如,哲学中有一个方法叫思想实验——用想象力去进行的实验,著名的如“缸中之脑”(美国哲学家希拉里·普特南1981年在他的《理性,真理与历史》一书中阐述的假想。大脑被从身体上切了下来,放进一个盛有维持脑存活营养液的缸中。脑的神经末梢连接在计算机上,这台计算机按照程序向脑传送信息,以使他保持一切完全正常的幻觉。有关这个假想的最基本的问题是:“你如何担保你自己不是在这种困境之中?”——记者注)。这是一个挺科幻的场景,在有的科幻电影(如《黑客帝国》)中也有所呈现。
哲学对科幻是一个启发,能给小说增加很多思考的空间。比如,科幻有一个常见主题是人与非人(机器人、外星人等)之间的关系。比较常见或者说简化的想法就是,双方要不谈恋爱,不要互相消灭。
但是在哲学范畴,我们要思考得更多。比如,当我们在处理人类和其他种族关系的时候,会面对一个深渊,双方在互相了解的过程中,不是简单的非敌即友关系。再比如,道德相对主义——道德到底是对所有人都一样,还是不同种族之间存在不同的道德准则。
中青报·中青网记者:你的日常写作状态是怎样的?
宝树:如果在家的话,我是“夜猫子”型的。白天有很多杂事,微信也总是打断你。如果睡得比较早,这一天就过完了,睡晚一点,还能有几个小时集中写作,往往凌晨两点睡觉算正常,3点也有,4点也有。还有人问过我,听音乐对写作有没有促进——我写作的时候从来不听,这会让人分神,我需要安静。
中青报·中青网记者:最近在读什么书?
宝树:科幻类的作品占了一半吧,如格雷格·伊根、伊安·班克斯、艾德里安·柴可夫斯基等国外作家;又如《金桃》《脑中之魔》《龙之变》等国内作家的最新长篇;也有纯文学和其他类型文学,像是《潮汐图》《一日顶流》《天下刀宗》,还有一些精彩的非虚构,比如《世上为什么要有图书馆》《猫鱼》。
中青报·中青网记者:就你的观察,目前国外流行什么科幻类型?
宝树:有一些是和中国相似的,比如高科技、外星人;还有一些是和国外所关心的社会议题密切相关的,比如种族、性别。美国非裔科幻作家杰米辛,以“破碎的星球”三部曲,分别获得2016-2018年雨果奖最佳长篇小说奖,创下纪录。小说讲的是种族从被压迫,到逐渐觉醒与反抗。
中青报·中青网记者:现在有越来越多的年轻人对科幻创作感兴趣,作为“过来人”,有什么基于自身经验的建议吗?
宝树:写东西的时候,首先就是要完成它。这像一句废话,但确实刚开始写的时候,很容易打退堂鼓,但努力写完之后,会给你很大的自信和动力。
中青报·中青网记者:你说过你的一个关注是,个体在一个科技发展狂野诡谲、价值观分崩离析的新时代,如何找到和安放自己的生活意义。你找到了吗?
宝树:在前现代,我们的理想状态是“一劳永逸”,和一个人共度一生,做一个工作直到退休。但现在,我们的生活已经很难做到“永恒”。就像书中《真爱》一文,提出一个问题:当人的寿命达到300来岁,婚姻还能持续多久?
生活的意义,已经不是“一劳永逸”,我们要找到的,是不同阶段的意义,是此时此刻值得的意义——将来也不后悔——这就足够了。
中青报·中青网记者 蒋肖斌来源:中国青年报
2025年10月17日 07版





 京公网安备 11010102004843号
京公网安备 11010102004843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