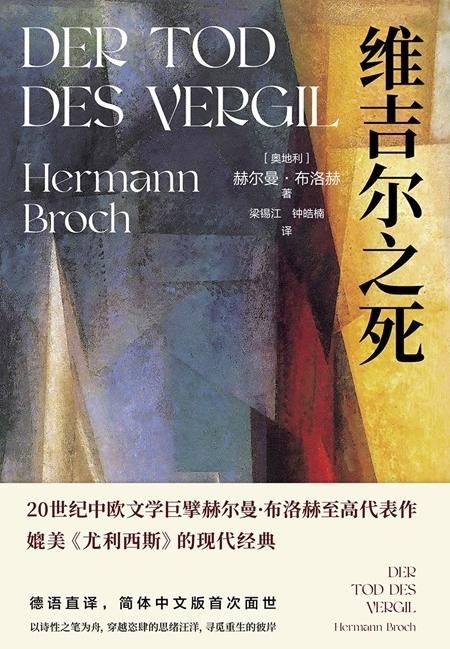
《维吉尔之死》书封">
文字瑰丽,只凭三言两语,便可以春秋笔法勾勒时代沧桑、风云变幻;文字贫瘠,纵使说千道万,也谈不尽人事代谢、命运无常。读赫尔曼·布洛赫总能给人这样深刻而独特的感受。
这是苦痛经历使然。赫尔曼目睹两次世界大战,他更饱经迫害和流亡之苦,将生命的热情投入到文学创作之中。赫尔曼的小说《着魔》《无罪者》《梦游人》……它们看似都在讲述无关铁血的故事,却总能让人感受到战争和暴政的疯狂与无情。
赫尔曼的述说,总是聚焦于人。他深刻意识到战争对人民的屠戮不只在身,更在于心,因此,他视线紧追战争狂热对人心道德的摧毁与撼动。赫尔曼认为价值崩溃时代下的人群心理是病态而脆弱的,小说《无罪者》中的人物看似都是远离战场的“无罪者”,但他们对于罪恶的冷漠、无知和盲从心理被赫尔曼袒露出来——其实他们都是“罪恶链”中的一环。
赫尔曼的眼光,一定凝望时代。若说他笔下的人物如同巴洛克珍珠,那么他同样擅长穿针引线;虽不谈及政治,但赫尔曼太懂得如何让一条珍珠项链在浸润时代底色中展现色彩。他可以化身但丁,为展现德国1913-1933年的时代图景,他用《神曲》般的诗歌隐喻时代残酷,暗讽战争狂热分子“满脑、满口地鼓吹着战争的神圣”。他可以成为乔伊斯,通过讲述一位游荡少年的内心沉浮,向读者展露他陷入迷狂的过程,军队制服如何成为他不想也无法脱掉的“一层皮”。他笔下的村镇甚至还能让人联想到鲁迅笔下的鲁镇,用“人血”满足各自的私欲和“道德”。这个角度讲,赫尔曼的多重面貌,还生动展现着不同时代的某些共性。
赫尔曼的希望,永远寄于自然。虽然生于苦难,但赫尔曼的文字从不被悲戚所浸染,让他还有着梭罗般的“田园气质”。赫尔曼的笔触为媒,大自然与各种动物总是具有美好的启迪意义,自然的生命力和迷狂人群的阴郁有机结合,形成了赫尔曼精妙独特的文学气质。赫尔曼在《着魔》中以一位乡村医生之口对自然进行告白:星辰“因所有的温柔变得温暖而轻盈”、夏日是一种“游荡、休憩的辉煌”、天空“像有弹性的瓷器”……感叹这些精巧修辞他是如何信手拈来的同时,我们甚至会忘记这部小说同时讲述的是以狂热和鲜血收尾的悲剧故事。
也许正因如此,赫尔曼才能被米兰·昆德拉誉为“中欧最伟大的作家”,他不仅用人物命运勾勒时代、折射思考,还借诗歌隐喻、风景描摹来糅杂美好与悲伤,意在昭示后人。然而,也正因为作品独特的隐喻、诗性和哲思,赫尔曼文字的精妙之处让翻译和理解变得困难,这也导致他的译本被许多国内读者翘首以盼数十年而不得。
2024年年底,赫尔曼“最为复杂的”“集大成之作”《维吉尔之死》终于在首次出版80年后出版中译本,许多学者认为这“填补了外国文学翻译的空白”。
事实表明,再精绝的语言表达都同时展现着瑰丽和贫瘠,赫尔曼及其作品展现的多重面貌不仅独一无二地展现着自己所处的时代故事,其在如今亦如同钻石般折射着不同时代、不同文化、不同语言的深邃内涵与光彩。
陈之琪来源:中国青年报
2025年10月17日 07版





 京公网安备 11010102004843号
京公网安备 11010102004843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