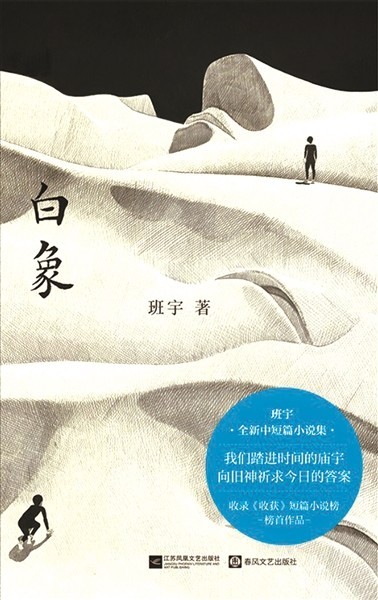
◎阿唐
班宇,1986年出生于辽宁省沈阳市,毕业于东北大学计算机系。2007年开始写乐评和文化专栏,曾用笔名坦克手贝吉塔,2016年起开始小说创作。
作品见于《收获》《当代》《十月》《上海文学》《作家》《山花》《小说界》等刊。曾获2019华语文学传媒最具潜力新人奖、GQ智族2019年度人物、《钟山》之星文学奖“年度青年作家奖”、花地文学榜短篇小说奖等。小说《逍遥游》入选“2018收获文学排行榜”,并获短篇小说类榜首。有小说集《冬泳》出版。
《白象》是班宇最新的小说集,里面收录的五个短篇小说,都指向了我们时代的罪和爱。这是一次更复杂也更冒险的探索,需要读者参与其中,填补、拼凑、想象、质疑,与他一同完成叙事,或一同戳穿小说叙事的诡计。
班宇在“序言”里说,我们读小说只能因为它什么也不是。在这本书中,与其说班宇创作了五个故事,不如说为我们展现了五次小说叙事的裂隙。在裂隙之间,我们会看到泥淖中的现实,也会看到班宇投射其上的诗性之微光。
叙事的诡计与裂隙
《清水心跳》里,导演对“我”的剧本提出意见:“你怎么写来写去,老是这么些个人,打麻将的,学英语的,装聋作哑的,知法犯法的,返城没有单位的,接了班又下岗的。”
这段文字很有趣,可看作班宇的自嘲。“东北文艺复兴”的旗帜太过于宏大火热,遮蔽了他在文本探索上的努力。所以,他在“序言”里说,这些小说“不是申冤在我,不是世纪的怀恋,也不是弱者的反叛”。实际上,他的小说里,始终充满对小说这种文体的质疑。这本书同样如此,不论独白、对话、意识流,或义正词严,或玩世不恭,都不可信。
在《飞鸟与地下》中,“我”和小柳对冬夜里飞鸟入窗的记忆全然不同。“我”的记忆里是一幅青春少女的奇幻画面,而小柳的记忆里却满是被遗弃的恐惧。因此,往后的若干年里,“我”被“愚人之链”困于当下,任由存在的印迹被他人抹去,小柳则始终在寻找过去与未来的连接,她注定化而为鸟,飞入深山。
在《狐及其友》里,“我”和小可皆在回避韩家勇之死,用各自的叙事来填充、遮蔽乃至篡改那段回忆。然而,“我”意识到,抹除关于韩家勇的记忆,韩家勇就真的“好像从没活过,从没存在过,没有任何痕迹”,这样一来,“我”存在的痕迹也随之抹去。最终,那只沙狐朝着“我”和小可走来,没有目的,也不寻求意义。
《关河令》由两段独白构成,两个讲述者都在自说自话。专车司机通过说话来消磨时间,因为“但凡一不说话,心里肯定就在琢磨事儿”。言语和思考产生裂隙,言语的所指不再是现实世界,因为那些事繁多、凌乱、不清晰,且无法触发行动。如司机所说,“那么多的事儿,琢磨得过来吗,能想明白吗。想明白了又能咋地。”于他而言,讲述这一行为本身就成了意义。
在结构更为复杂的《白象》中,不同角色的叙事相互矛盾,互为补充,而每个角色的叙事——如李东方临终前的讲述也是断断续续的,需要提炼重点,“整个叙述相当混乱,其间也有反复”。“我”试着拼凑,却从未成功。这让人想起“盲人摸象”的成语,通过几片零碎的叙事,是否能拼凑成完整的故事?倘若真能拼凑起来,我们限于自己的视角,又该如何去认识它?
《清水心跳》更为冒险,班宇毫不保留地揭开了叙事的表层,袒露其肌理与内脏,让我们看见其创作过程,其中陈列着不完整的构思和不顺畅的讲述。他在“序言”里说,《清水心跳》里的每个人都没有心跳。因为“我”和赵晓初都在各自的叙事轨道上,只是两条轨道最终相交于同一个现实,其结果或是交融,或是相撞。
在这五篇小说里,班宇为我们呈现了多种叙事的可能,破碎的、矛盾的、虚伪的、不甘的、逃避的……这大概就是小说这种文体的优势,它由叙事构成,同时可以戳穿叙事的诡计。
罪的遗传与救赎
当叙事受到质疑,角色的讲述会在矛盾下相撞,我们得以穿透裂隙,窥见现实的泥淖,以及从未止息的罪与爱。这本书里的每篇小说都和罪有关,爱自然就成了我们的救赎之路。
在《白象》这篇小说里,三辈人的讲述共同钩织成一张罪过之网:冯兆兴因怯弱,在胡荣灿的判决书上签了字;李东方因怯懦,在冯少宝夫妇遇难之际选择回避,又为了私利而检举胡林;胡林灰心丧气、沉迷赌钱,导致妻子在精神失常的状态下诬告了冯少宝……
凡此种种,皆如冯兆兴自省,他是怯懦、消沉的“有罪之人”,没有任何去处,我们未尝不是。或许,我们也会存有胡林一样的侥幸,认为一切似乎可以重新开始。然而,罪过渗入血液,继续涌动、流淌、遗传,如怪物般自行生长,直至吞噬后辈的人生。
在《白象》中,困在网中的不只有李东方、胡林等人,还有“我”和胡晓雪。每一代人在享受上一代人荣光的同时,也背负着他们留下的罪过。自降生那一刻起,世界已经如是,我们别无他处可去。
在祖辈胡荣灿创作的戏剧里,白象仿佛偶然闯入现实世界的克苏鲁,它的身前是夺命奔逃的人们,身后是凌乱的废墟。到了胡晓雪家里,白象化作了细腻洁白的玉器,躲进玻璃柜深处。即便这样,这只白象仍让“我”感到恐惧。它仿佛会随时醒来,冲向人们,“踏过街道、桥梁与房屋,无人可以驯服”。难怪冯少宝临终前对赵玉莲说,“一匹白象,害我半生,今天我砸了你。”
同样,《飞鸟与地下》里小柳在寒冬里推开的窗,《狐及其友》里“我”在深夜里点燃的舞厅,《关河令》里在嘈杂中倒塌的墙,《清水心跳》里李小天在泥坑里掉落的书,皆是被回避、被篡改、被遗忘的罪的记忆,它们藏在人的心底,终其一生都在抓挠、咬啮。
以自身遭遇痛斥时代荒谬的一代,也并未让罪止住,下一代仍需寻求赎罪之路。《白象》里,在“我”的眼中,父亲李东方像个失败的锁匠,挂着满身钥匙却一个锁也打不开,而真正挂着满身钥匙的胡晓雪,却带着“我”穿过一扇扇门,让“我”回到屋子中央那块水磨地面。
值得留意的是,胡晓雪、小柳、小可、赵晓初都与“我”再次相遇,仿佛命中注定。究其原因,虽然“我”未必是罪的制造者,但唯有“我”意识到罪的存在,也只有经由“我”,我们才能找到救赎之路,这条路就是诗的写作。
诗与爱的微光
写小说之前,班宇写过很多年的乐评。他的小说里,对音乐的描写俯拾即是。除了赋予音乐以形状、颜色、温度,他的对话里还时常化用歌词。中国古典诗词中,鲜少提及东北的历史及风物,人们找不到可以抒情言志的意象,歌词或许是为数不多的依托。
李东方在医院唱着费翔的“我,曾经豪情万丈,归来却,空空的行囊”;韩家勇在歌厅唱着张雨生的“我的未来不是梦,我认真地过每一分钟”;专车司机想知道左小祖咒那句“你在下雨的夜给我打了个电话”到底是什么歌……
班宇的小说是诗,小说里的人物却说着方言。方言与诗之间的沟壑由音乐和歌词填补,因而,人物始终在幽默和虚无中透着精神的力量,如冯兆兴蟋蟀般对着瓮中的四壁吹口哨,如胡荣灿唱着庄严弥撒赴死。
除了语言,班宇的意象也富有诗意:温润光泽的白象,如箭离弦的鸟,迎面走来的沙狐,淅淅沥沥的雨,可容人藏身的植被……然而,诗并非只是温文尔雅,它也有另一种面相,如白象踏过的废墟,巨大云杉构成的迷宫,黢黑墙上的火苗印迹,轰然坍塌的墙,夜晚音乐里喧嚣的狗吠……
当温文尔雅与粗粝冷峻混在一起,诗的力量就会爆发,穿透叙事的裂隙,在泥淖中投以微光。所以,班宇的小说会让人愤怒,让人难过,同时也让人温暖,让人感到希望。
这一切都关乎爱与友谊:在《白象》结尾,白象从“我”怀中走出来,“我”渴望胡晓雪找到“我”,递过来一只手,带“我”离开;在《飞鸟与地下》结尾,小柳在深林里拉住“我”的手,让“我”感到时间、未知与爱,具体地来到面前;在《狐及其友》结尾,沙狐朝着“我”与小可走来;《关河令》以友人追悼会上的反思收尾;在《清水心跳》的最后,赵晓初靠在“我”身上,“我”渴望与她这样走下去,也希望把小说继续写下去。
那么,小说究竟是什么呢?或许真如班宇所说,在今天,人们写它、读它,皆因其什么都不是。我们正是在种种“不是”之间,寻找“短暂而渺茫的确切”。这一点确切的微光,或许就是爱与友谊,我们在彼此身影的陪伴下,踏上救赎之路。





 京公网安备 11010102004843号
京公网安备 11010102004843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