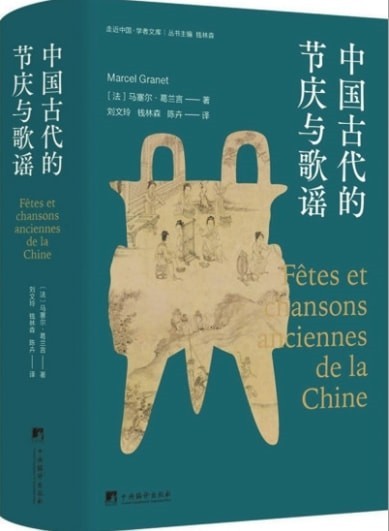

◎董继梅
《诗经》中的情歌是古代中国人热烈与忧伤的情感表达,奠定了中国抒情诗的基石。然而法国学者葛兰言从语文学与社会学的视角,认为这些歌谣是人们在上古季节性集体仪式中的口头表演产物。它们最初承载着协调人与自然、整合社会共同体的宗教性功能,是古老祭坛与旷野集会的原始和声。人们试图通过节庆仪式中的口头即兴创作与自然力量沟通,联结个体与群体,从而在自然与社会中确立良好的秩序。故而,《诗经》情歌不再是纯粹的民间爱情诗,而是体现了中国上古宗教从“民间习俗”到“官方祀典”这一动态演变过程的珍贵文献。
从“民间习俗”到“官方祀典”
“春日载阳,有鸣仓庚”,当节庆的季候性轮盘缓缓转动,乡民们如自然一般依时行事,从各个角落聚集定期集会。在节庆仪式中,人们会围绕预先规定的主题(如求偶、祭祖等)进行口头即兴创作。如《郑风·溱洧》描写上巳节男人和女人在溱水和洧水边集会、嬉戏、观览,展现了一幅活泼奔放的生命画卷。《召南·采蘩》描写人们去河川采摘白蒿用于祭祖,及盛装去祭祀的场景,内蕴古代中国人在宗庙祭祀中庄重虔诚的礼制精神。这些歌谣呈现出中国社会“俗”与“礼”交织互动的生动图景。在这些节庆中,通常会有赛歌的活动来表达情感。仪式中的赛歌活动潜移默化地将社会规范内化为个体的情感表达方式,不仅能宣泄情感、促进两性交往,还可以加强个体与群体的联结,巩固“社会公约”的仪式化。
这种通过共同创作与聆听建立的即时联结,比任何说教都更能让人切身感受到“我们”的群体认同感。集会的山川因此超越了简单娱乐的物理空间,成为共同体叙事的神圣空间。在这里,情感宣泄与道德教化、个体价值与集体认同和谐地融为一体。情歌成为信仰习俗的象征性表达,呈现了上古先民们的宗教生活场景。民间习俗成为建构封建国家祭祀礼仪与社会道德秩序的重要来源。
《诗经》情歌中直白、细致的古老习俗描写是“乡野仪礼”的表演文本,经过历代儒学阐释者们忽略或淡化狂欢的细节后,成为“依时”“和谐”“慕偶以正”等符合良好社会秩序的道德法则。一方面抽离民间节庆中崇拜神圣山川自然力、顺应时令等价值观念,保留其“序天地、和人神”的道德秩序追求,并将其嫁接到封建王朝国家祭祀体系中,使得歌谣与信仰在节庆中“暂时共存”。故而,《诗经》情歌也成为研究信仰起源与分化的珍贵文献。在这些情歌中,可以看到,中国古代原本混融一体的民间季候性庆典,随着社会的复杂化,发生了功能性分化。一部分狂欢的习俗被抑制或边缘化,而其中能够协调自然界与社会秩序的习俗被提炼和改造,用于建构“封建国家”和“士大夫阶层”的仪礼,演变为封建王朝国家的祭祀活动,确立道德秩序。
歌谣从习俗到礼制、从民间到官方的动态演化,体现了中国文化中“俗”与“礼”之间的深层关系,奠定了后世中国人宗教生活与道德观念中重视秩序、和谐与现世实践的基本底色。汉初《周礼》剥离了《诗经》中的情感,将节庆仪式纳入国家行政管理和礼乐教化的框架之中,清晰而详细地规定了不同官职在各类祭祀、庆典中的职责与礼仪程序,注重节庆对民众的教化与调节作用,构建了一套服务于国家治理的节庆体系。
这套体系奠定了后世两千余年中华帝国官方祭祀与庆典的基本模式,使得节庆不仅关乎民俗与情感,更成为维护“天下秩序”的一种重要政治技术。汉代的《礼记·月令》对节庆仪式的描述更是依时序,将民间习俗纳入国家礼制,为汉代以后节日体系的形成提供理论框架。至此,中国古代社会基本完成了从民间习俗到国家祀典的演化。《诗经》见证了从民间仪式性口头表演到道德教化的国家祀典这一漫长过程的起点。
建构我们的共同体叙事
有关艺术与仪式的关系问题,与葛兰言同时代的英国学者哈里森,结合现代考古学发现与古典文献,考察了古希腊宗教仪式与艺术的关系。她提出艺术与仪式共同源于人类情感的具象化表达,从而厘清了古代艺术与原始仪式之间的逻辑关系。葛兰言在《诗经》情歌和节庆仪式中找到内在逻辑,继承和吸收了涂尔干、莫斯的宗教社会学方法论,考察中国古代的宗教习俗与《诗经》之间的关系,分析中国古代节庆、婚姻、礼仪,揭示其背后的集体意识和社会整合功能,理解中国文明的内生逻辑。葛兰言认为歌谣起源于集体仪式表演,在庆典中的赛歌活动产生强烈的情感力量,联结个体与集体,实现共同体叙事。他认为,在春季,人们通过两性对抗的竞赛和共同体,促进了各个地方集团对一个传统共同体的融入。这样的论述,有利于我们探讨传统节日文化的当代价值,有利于建构我们的共同体叙事,强化共同体意识。
葛兰言对《诗经》情歌的阐释,运用语文学和社会学的方法,从节庆仪式中古老的歌谣去理解背后的中国古代宗教与社会,阐明了中国古代节庆活动中社会联结与文化隐喻的形成过程。葛兰言一直在不遗余力地批判19世纪至20世纪初主导汉学研究的实证主义语文学范式。他认为《诗经》这样源于集体、口头传统的文本,如果脱离节庆的语境去进行谱系性的追溯,会掩盖其作为社会事实与仪式实践的本质,是没有意义的徒劳。他从汉学语文学研究方法转向宗教社会学研究方法,关注文本作为社会现象,揭示了怎样的社会事实,而不是关注文本诉说了什么样的历史。
然而,葛兰言对语文学研究方法始终是矛盾的,他一方面批判,一方面却是基于文本材料,将《诗经》情歌的语文学微观分析服务于社会学的宏观构想。他认为汉儒的伦理化诠释,恰恰证明了封建国家如何系统地“误读”并收编民间传统,进行道德教化的建构,以适应新的社会秩序。实质上,葛兰言在语文学研究的基础上,批判性地继承,进行了一场语文学的社会学化改造。他将语文学对文本细读的关照,转向了对社会形态与集体表征的解读,将歌谣视为古代集体情感的载体,阐释其对中国早期社会结构及文明制度的奠基作用。这一跨学科研究的洞见,至今依然能给我们的研究很多启发,仍能激发我们对方法论、文本阐释与文化记忆的再思考。
有敏锐的洞见但也存在明显的偏颇
当然,葛兰言的论断虽然能直叩信仰的本源,有其敏锐的洞见,但也确实存在明显的偏颇与过度的简化。他认为社会必须通过周期性的集体仪式来重申自身,实现“再生产”,他将《诗经》情歌文本中的“邂逅”“赠答”“思念”解释为神圣仪式的口头表演,是一种诗歌形式的注脚,而非个体的情感记录。这种整体性和功能性的解释框架,扩宽了歌谣的研究范式,但也难免限于结构性功能的诠释,存在着宗教社会学方法的局限与经验的偏差,消解了创作个体的主体性,一定程度忽视了文本丰富性和个体的生命体验。他强调集体口头创作的观念,模糊了个体特性,遮蔽了读者主体。他聚焦于作品产生的原初社会语境,而对作品在后续历史中如何被不同社会力量挪用、诠释与经典化的过程关注不足。但葛兰言对传统的深刻理解和大胆反叛,基于“矛盾心理”拉锯而催生的创造性张力,给我们带来了一定的启示与思考。





 京公网安备 11010102004843号
京公网安备 11010102004843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