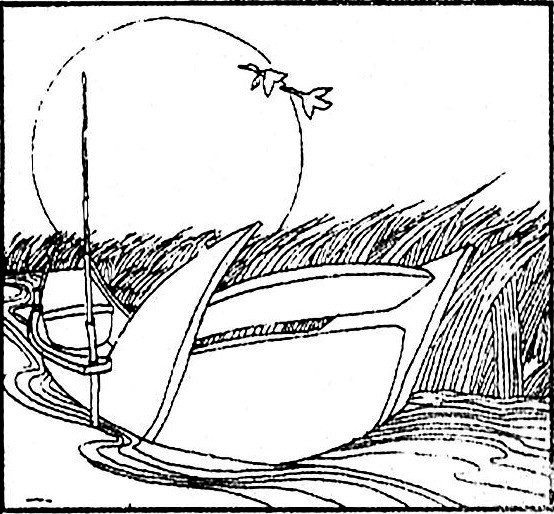
根据汪曾祺《大淖记事》改编的同名连环画作品 资料图片

《中华读书报》“枕边书”系列文章 资料图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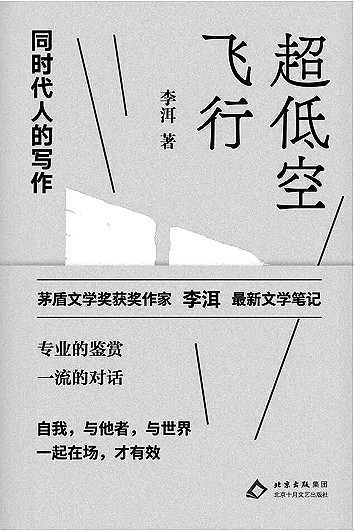
创作谈在文类层面成为“类创作”,作家纷纷推出文论专著。资料图片
【畅谈“创作谈”】
一部作品被作家创作完成,就独自开启一段旅程,沿途可能邂逅不同的读者,他们在阅读欣赏与审美接受的过程中绘制出不同的“风景”。但仍然有许多作家有意犹未尽之感,对读者甚至对自己还有话要说。于是,自序、跋、后记、访谈录、对话等不同文体样式的作家随笔与作品相伴相生、携手同行,这些通常被称为“作家创作谈”。
这些文字的背后,隐隐地拖曳着作家、作品长长的影子,有助于我们更深入地沉潜文本,在作家的语汇间捕捉思绪与灵魂的经纬。可以说,创作谈是作家通过回望与检视,对自己写作经验进行总结和思辨,饱含着作家对文学深沉的思考。同时,它也在一定程度上体现了作家在精神维度上的深切叩问和自我反省,对所处时代的深层理解与深刻感悟。这些思考彰显出创作主体的内在追求,也成为读者深度参与作家“写作发生”的端口。
创作谈有助于重新“发现”作品
作家的创作谈或文论可以有效参与作品的阐释,其中蕴含着他们对社会世情的关切和情感体察的深度,在共情之中实现文本的“溢出”和对文本的“养分补给”。持续写作几十年的作家,大都在不同形式的创作谈里,坦言自己在写作过程中遭遇的问题、困惑、瑕疵和局限,包括许多写作发生时的“内情”和直觉,甚至是“错觉”。在内省的自觉之外,作家也在创作谈中论及自己的写作经历,或是悉数创作历程的心迹,或是将写作的发生与转折点铺陈其中,令读者更为准确地捕捉文本的“题中应有之义”,从而规避脱离文本的“误读”。
汪曾祺在《〈大淖记事〉是怎么写出来的》中,详细而朴实地讲述了这篇小说从酝酿、构思到落笔成文的整个过程,其中说及的一处细节令人动容。小说中,巧云的恋人奄奄一息,当地的说法是要喝陈年尿桶里刮出来的尿碱。巧云给恋人灌了一口,“不知道为什么,她自己也尝了一口”。在创作谈中,汪曾祺写道:“这是我原来没有想到的。只是写到那里,出于感情的需要,我迫切地要写出这一句(写这一句时,我流了眼泪)。”
或许在大多数读者眼中,故事和人物的结局更加受人关注,然而,这一唯有真情方能使然的“情急之下”与“自然而然”,包括作家本人行笔至此时的情感抒发,亦是生动的“情感教育”。或许在这里,小说与创作谈的情感同构,真正实现了汪曾祺的老师沈从文所传授的“在写作过程中要随时紧紧贴着人物,用自己的心,自己的全部感情”。这篇短文与相对应的小说如同“镜与灯”,相互映照,钩沉出叙事内外的丰沛、妙趣和隽永的诗意,让文本焕发出恒久的魅力。可以说,汪曾祺在创作谈中表达了写作时对生活经验的“咀嚼”和审美转化,以及他构想人物和故事的深意。这样的创作谈,彰显出作家撷取生活精微的悟性和睿智。此外,汪曾祺诸多专门性文论,也构成我们重新“发现”作品、检索写作心理、探寻精神原型的重要参照。
创作谈与作品之间形成互文关系
透过创作谈,作家往往表述自己“思于他处”“内秀于中”的情思,向读者透露作家、作品、生活之间复杂而隐秘的精神联系,不仅延伸了叙事的内涵,也生成与之密切相关、意味隽永的互文,成为作家灵感的溯源,引领读者一同回望作家创作的起点与征途。
贾平凹经常在创作之外为自己的作品写序言、后记等。在《商州:说不尽的故事》的序言里,他说:“商州曾经是我认识世界的一个法门。虽然也是饮食男女,家长里短,俗情是非,其实都是基于对我们民族过去、现在和未来认识的一种幻想。”他在《秦腔》后记中写道:“现在我为故乡写这本书,却是为了忘却的回忆。我决心以这本书为故乡树起一块碑子。”从这些表述中,我们看到一位专注于乡土书写的作家,通过写作所体味到的生活真谛、人生百态,传递出对乡土、民族和人类命运的深切关注。透过这些可以看出,创作谈在一定程度上不仅作为作家文本的某种“画外音”,是一种叙事的“补遗”,弥补写作留下的未竟憾事,同时也缓释写作中的诸多甘苦,记录、见证作家的精神成长历程。
随着作家主体性的日渐凸显,创作谈拓展出更为宏阔的价值向度,开始更多地从写作背后所深隐的个体感悟,延伸向认识世界、探索世界的法门和要义。《中华读书报》推出“枕边书”系列文章,主要追踪作家的“阅读史”轨迹。就兼具学者、教师、小说家身份的格非而言,他的“枕边书”往往是随笔、杂录、笔记、哲学小品、历史评论、方志、博物志一类的闲书和杂书,包括《道德箴言录》《世说新语》《梦溪笔谈》《扬州画舫录》《容斋随笔》,以及大量的诗歌作品。我们由此也对作家的知识谱系、看待世界的眼光、创作意图与关注对象产生“合理的想象”。这些“作家书单”为读者增添了小说之外的阅读可能性,唤起了人们阅读典籍、志书、世界经典著述的冲动。由这一路径可以看出,创作谈让读者以更加主动的姿态走进作家的精神世界。这份“合理的想象”可以转化为强烈的阅读驱动力。在这个过程中,读者的阅读边界被不断拓宽,从而收获跨文本、跨时空的思考维度,让阅读成为真正的精神互动。
此外,王安忆的《心灵世界》、毕飞宇的《小说课》、苏童的《小说是灵魂的逆光》等作家文论专著,是理解作家创作的重要资源。可以说,创作谈在文类层面亦演变为一种专门性的“类创作”,生成独特的文体价值与意义。近年来,李洱的《超低空飞行:同时代人的写作》成为作家文论的力作之一。他不仅回顾了小说《石榴树上结樱桃》《应物兄》中现实投影的深思,阐述对“同时代人”写作的理解,还对想象中国的方式、传统与现代的关联、大众传媒如何影响生活、写作与批评的对话关系等问题进行了剖析。这些深刻的思考已经超出知识传递的范畴,体现出写作者虔诚的“行动”姿态。
新媒介语境下创作谈的新变
在“大文学观”背景下,文学生产、传播、接受迎来变革与挑战,“短视频、直播、社交媒体与算法分发并不只是新的传播渠道,它们重塑了叙事逻辑”,创作谈的样式和内涵也随之出现新的变化。余华的小说创作和创作谈深度参与并且展现了这个变化过程。他的小说历经国内外多次再版和译介,通过不同版本的序言,可以大体爬梳出他“写作发生”的心路历程,也可以梳理出他对读者声音的回应。这些序言在“读”与“写”之间创设了心灵交汇的具象化对话空间。近年来,他在《我们在岛屿读书》《一直游到海水变蓝》等节目中不断“破圈”,延伸出关于“余华的书单”“重读余华”等热门话题。由此可见,在新媒体时代,原本作为文本的衍生物或是作家附言的创作谈,不仅在文类上占据“一席之地”,也开始从“幕后”走向“台前”,迎来独立发声的可能。
许多作家的创作谈以短视频的方式呈现,更加便捷地出现在读者视野之中,构成有力的介入性辐射,搭建起写作者与阅读者之间进一步交流的桥梁。此外,各类自媒体平台也往往将创作谈视为网络推文的标配,这些连缀成篇的“外传”成为还原作家及其创作的“密钥”,读者不仅能在文本的尾声看见创作谈“真容”,也可以从更多端口了解作家的“未尽之言”。
创作谈与媒体传播和出版物构成深度互动,这种跨媒介的新型创作谈模式,呈现出文学的“破圈”之势。苏童的长篇小说《好天气》出版之后,名为“苏童的世界”的视频号发布多个短视频,谈及《好天气》与他以往小说的差异和联结。麦家、叶兆言、鲁敏、班宇等作家纷纷通过新媒体平台讲述创作心得。而文学栏目“文学的故乡”“文化跨年·世界在望”“文学的日常”等“策划性创作谈”也广受关注。我们得以知道,贾平凹跟随同乡遍访秦岭,对故乡的意义有了新的认知,他在小说中传递的“人活一世,草木一秋”的人文关怀显得更加深刻。我们也在青年作家双雪涛略带羞赧的朗读声中,穿越作家生动的情感,理解小说《猎人》中所写的外婆煮的那碗“猪肚萝卜汤”足以冲淡现实迷惘的灵魂力量。在画面、声音、小说文本搭建而成的“综合场景”中,读者可以透过这些屏上的创作谈进一步了解作家与作品,进而理解时代和身处的世界。通过新媒体平台所创设的“新现场”,作家们以更加鲜活的面貌诉说创作心境、回溯文化情思,显现出“时刻在线”的创作生机,也展现出积极应对时代发展变化的在场活力。
值得注意的是,作家创作谈固然是重要的阐释资源之一,但并非唯一标准,因而,读者应当警惕陷入“作者意图决定论”,这也向作家提出力避“自说自话”“一言堂”的要求。在当下,创作谈的价值正在不断焕发出新的时代活力。我们始终都在寻找能在刹那间照亮作品时空和生命情思的那束光。作家的创作谈或许就是那束光,可以让整个作品亮堂起来,向无穷远方敞开。
(作者:张学昕、任子钰,分别系辽宁师范大学文学院教授、博士研究生)





 京公网安备 11010102004843号
京公网安备 11010102004843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