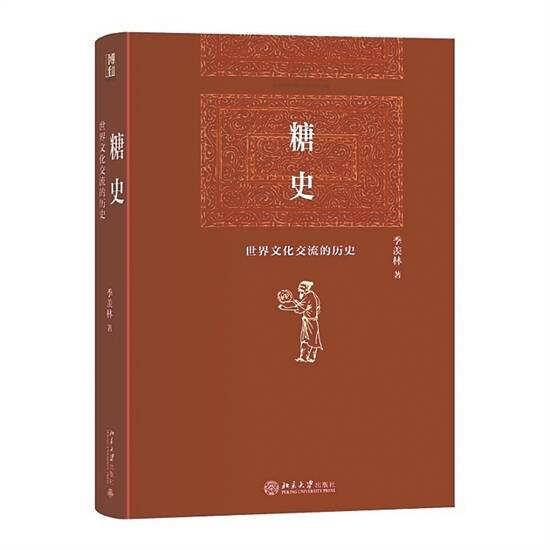
季羡林
2025年12月,季羡林先生著《糖史》完整版再次重印,特此摘发季老生前所撰书序——
一言以蔽之,我写《糖史》,与其说是写科学技术史,毋宁说是写文化交流史。既然写《糖史》,完全不讲科技方面的问题,那是根本不可能的。但是,我的重点始终是放在文化交流上。在这一点上,我同李约瑟的《中国科学技术史》是有所不同的。
我之所以下定决心,不辞劳瘁,写这样一部书,其中颇有一些偶然的成分。我学习了梵文以后,开始注意到一个有趣的现象:欧美许多语言中(即所谓印欧语系的语言)表示“糖”这个食品的字,英文是sugar,德文是Zucker,法文是sucre,俄文是caxap,其他语言大同小异,不再列举。表示“冰糖”或“水果糖”的字是:英文candy,德文Kandis,法文candi,其他语言也有类似的字。这些字都是外来语,根源就是梵文的arkar。根据语言流变的规律,一个国家没有某一件东西,这件东西从外国传入,连名字也带了进来,在这个国家成为音译字。在中国,眼前的例子就多得很,比如咖啡、可可等,还有啤酒、苹果派等,举不胜举。“糖”等借用外来语,就说明欧洲原来没有糖,而印度则有。实物同名字一同传进来,这就是文化交流。
先秦时期,中国已经有了甘蔗,当时写作“柘”。中国可能还有原生蔗,但只饮蔗浆,或者生吃。到了比较晚的时期,才用来造糖。据《新唐书》卷二二一上的《西域列传·摩揭陀》的记载,唐太宗派人到印度去学习熬糖法。真是无巧不成书,到了20世纪80年代初,有人拿给我一个敦煌残卷,上面记载着印度熬糖的技术。唐太宗派人到印度学习的可能就是这一套技术。我在解读之余,对糖这种东西的传播就产生了兴趣。后来眼界又逐渐扩大,扩大到波斯和阿拉伯国家。这些国家都对糖这种东西和代表这种东西的字的传播起过重要的、不可或缺的作用。我的兴致更高了。我大概是天生一个杂家胚子,于是我怦然心动,在本来已经够杂的研究范围中又加上了一项接近科学技术的糖史这一个选题。
关于糖史,外国学者早已经有了一些专著和论文,比如德文有von Lippmann的《糖史》和von Hinüber的论文;英文有Deerr的《糖史》等。印度当然也有,但命名为《糖史》的著作却没有。尽管著作这样多,但真正从文化交流的角度上来写的,我是“始作俑者”。也正是由于这个原因,我的《糖史》纯粹限于蔗糖;用粮食做成的麦芽糖之类,因为同文化交流无关,所以我都略而不谈。严格讲起来,我这一部书应该称为《蔗糖史》。
同von Lippmann和Deerr的两部《糖史》比较起来,我这部书还有另外一个特点。我的书虽然分为“国内编”和“国际编”,但是我的重点是放在国内的。在国际上,我的重点是放在广义的东方和拉美上的。原因也很简单:上述两书对我国讲得惊人的简单,Deerr书中还有不少的错误。对东方讲得也不够详细。人弃我取,人详我略,于是我对欧洲稍有涉及,而详于中、印、波(伊朗)、阿(阿拉伯国家,包括埃及和伊拉克等地)。我注意的是这些国家和地区间的互相影响的关系。南洋群岛在制糖方面起过重要的作用,因此对这里也有专章叙述,对日本也是如此。
写历史,必须有资料,论从史出,这几乎已成为史学工作者的ABC。但是中国过去的“以论代史”的做法至今流风未息。前几天,会见一位韩国高丽大学的教授,谈到一部在中国颇被推重的书,他只淡淡地说了一句话:“理论多而材料少。”这真是一语破的,我颇讶此君之卓识。我虽无能,但绝不蹈这个覆辙。
可是关于糖史的资料,是非常难找的。上述的两部专著和论文,再加上中国学者李治寰先生的《中国食糖史稿》,都有些可用的资料;但都远远不够,我几乎是另起炉灶,其难可知。一无现成的索引,二少可用的线索,在茫茫的书海中,我就像大海捞针。
蔗和糖,同盐和茶比较起来,其资料之多寡繁简,直如天壤之别。但是,既然要干,就只好“下定决心,不怕牺牲”了。我眼前只有一条路,就是采用最简单、最原始、最愚笨,然而又非此不可的办法,在一本本的书中,有时候是厚而且重的巨册中,一行行,一页页地看下去,找自己要找的东西。我主要利用的是《四库全书》,还有中国台湾出版的几大套像《丛书集成》《中华文史论丛》等一系列大型的丛书。《四库全书》虽有人称之为“四库残书”,其实“残”的仅占极小一部分,不能以偏概全。它把古代许多重要的典籍集中在一起,又加以排比分类,还给每一部书都写了“提要”,这大大地便利了像我这样的读者。否则,要我把需用的书一本一本地去借,光是时间就不知要花费多少。我现在之所以热心帮助编纂《四库全书存目丛书》,原因也就在这里。我相信它会很有用,而且能大大地节约读者的时间。此外,当然还有保存古籍的作用。这不在话下。
然而利用这些大书,也并不容易。在将近两年的时间内,我几乎天天跑一趟北大图书馆,来回五六里,酷暑寒冬,暴雨大雪,都不能阻我来往。习惯既已养成,一走进善本部或教员阅览室,不需什么转轨,立即进入角色。从书架上取下像石头一般重的大书,睁开昏花的老眼,一行行地看下去。古人说“目下十行”,形容看书之快。我则是皇天不负苦心人,养成了目下二十行,目下半页的“特异功能”。但是,天底下的事情总不会尽如人意的。有时候,枯坐几小时,眼花心颤,却一条资料也找不到。此时茫然,嗒然,拖着沉重的老腿,走回家来。
就这样,我拼搏了将近两年。我没有做过详细的统计,不知道自己究竟翻了多少书,但估计恐怕要有几十万页。我绝不敢说没有遗漏,那是根本不可能的。但是,我自信,太大太多的遗漏是不会有的。我也决不敢说,所有与蔗和糖有关的典籍我都查到了,那更是根本不可能的。我只能说,我的力量尽到了,我的学术良心得到安慰了,如此而已。





 京公网安备 11010102004843号
京公网安备 11010102004843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