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包罗万象
发稿时间:2019-07-31 17:15:00 来源:中国青年网
这些概念可能有些晦涩,毕竟人类已经遍布全球,且踏无止境。我们几乎到过这颗蓝色星球的每个角落,还有人甚至飞离过地球。想象我们的肠道或细胞里自有天地乾坤,身体内部也有若起若伏的体貌风景,这多少有些奇怪。然而事实就是如此。地球表面有各种各样的生态系统:雨林、草原、珊瑚礁、沙漠、盐碱地,每一种系统内都分布着不同的生物种群。而每个动物身上也都分布着不同的生态系统:皮肤、嘴、肠胃、生殖器,以及任何与外界相连的器官——各处都分布着独特的微生物群。我们只能通过卫星俯瞰横跨大洲的生态系统,但生态学家可以使用术语和概念来帮助我们凝视自己体内的微生物群。我们可以谈论微生物的多样性,通过绘制食物链(网)来描述不同有机体之间的“捕食”关系。我们也能挑出某种关键的微生物——它们能和海獭或狼群一样,对整个环境造成与其数量不成比例的影响。我们可以把致病微生物(即病原体)定性为入侵物种,就像对待海蟾蜍或火蚁。我们可以把炎性肠病患者的内脏比作垂死的珊瑚礁或休耕田:一个受损的生态系统,其内部不同有机体之间的平衡都已打破。
这种相似性意味着,我们观察白蚁、海绵或老鼠时,也相当于在观察自身。它们身上的微生物或许与我们不同,但是都遵循相同的生存规律。与发光菌共生的乌贼只在夜间发光,而我们肠道内的细菌,每日也遵循类似的涨落起止节律。珊瑚礁里的微生物因为经历污染和过度捕捞而变得杀气腾腾,人类肠道中的菌群在不健康的食物或抗生素的侵袭下也会发生奔涌的腹泻。老鼠肠道中的微生物会左右它们的行为,而我们自己肠道内的伙伴也可能潜移默化地影响我们的大脑。通过微生物,我们能够发现自己与大大小小不同物种间的共通之处。没有一个物种独自生存着,所有生命都居于布满微生物的环境之中,持久地往来、互动。微生物也会在动物之间迁移,在人体与土地、水、空气、建筑以及周围的环境之间跋涉,它们使我们彼此相连,也使我们与世界相连。
所有的动物学都是生态学。如果不理解我们身上的微生物,以及我们与微生物之间的共生关系,我们就无法完全理解动物的生命运作。微生物如何丰富和影响了其他动物?只有探究清楚这些问题,我们才能充分认识自己与体内微生物组间的羁绊。我们需要放眼整个动物界,同时也聚焦到隐藏在每个生命体中的生态系统。我们在观察甲虫与大象、海胆与蚯蚓、父母与朋友时,看到的都是由无数细胞组成的个体:由一颗独立的大脑指导行为,通过基因组调控生命活动。但这只是一个便于理解的假想系统。事实上,我们每个人都是一支军团,从来都是“我们”,而不是“我”。忘记奥逊·威尔斯口中的“孤独”吧,请听从沃尔特·惠特曼(Walt Whitman)的诗语:“我辽阔博大,我包罗万象。”
404 Not Found
- 帮视障书友共享阅读之乐
- 范仲淹 以读书为家训
- 第五批3种重点领域国家安全普及读本出版发行
- 图像时代,让文学回归文字
- 《袁同礼年谱长编》:十年磨剑 既博且精
- 《扬兮镇诗篇》:“诗”与“远方”的对话
- 《金石昆虫草木状》:万物诗意 流诸笔端
- 在泥蜂舍 编虫子书
- 屈原:为法制事业而献身的改革家
- 以文学之笔书写文明交融之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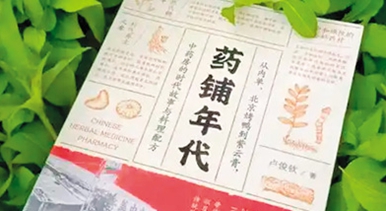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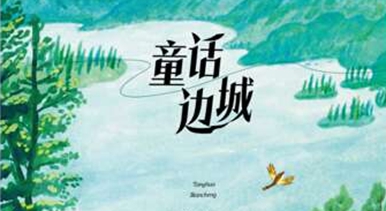






 京公网安备 11010102004843号
京公网安备 11010102004843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