艺术是个奇异之物 章诒和:梅兰芳的戏“空前绝后”
发稿时间:2017-03-08 13:35:00 来源:中国青年网
此外还有一个情况,极有可能就是发生在黄裳观看梅氏演出而大发议论之日,梅兰芳恰逢突如其来的变故。1947年1月5日,他最为心爱的弟子李世芳因飞机失事而罹难。梅兰芳在《舞台生活四十年》里记述说:
回想四年前在上海中国大戏院,李世芳陪着我唱青蛇,这还是我演《金山寺》带《断桥》的初次尝试。他并不是我们剧团的人,临时约他参加帮忙,前后演了几场,我都觉得满意。我记得1947年1月2日的晚上,我们演完了最后一场,他在5日早晨坐了飞机回北京。飞到青岛,半路上飞机出了事,把他牺牲在里面,我们师生从此就永别了。我那天正在后台扮戏,听到这个传说,差一点要晕过去。旁边有人安慰我说,“这消息不一定可靠”。我还希望这不是事实呢。谁知道第二天我接到飞机场的电话,竟证实了这件惨事。我大哭了几场,从此就不愿意再演这两出戏。
年仅二十六岁的李世芳,夙有“小梅兰芳”之称,位居“四小名旦”之首,是公认的梅兰芳艺术的继承者。李世芳之死,对于梅兰芳的打击是相当沉重的。而黄裳的那篇不顾实际情况,并且不合时宜的批评文章,客观上不能不说是对于梅兰芳的伤害。黄裳却始终不肯认这笔账,晚年犹是嘴硬,写文章为自己辩护说:
我写过不少评梅戏的文章,大抵喜欢的多说一点,不大喜欢的少说一些,但从未放过冷枪。对他早年的反串戏,我也并不认为是他的代表作,未能一律吹捧。就在《饯梅兰芳》一文中,也指出了他的一些缺点,如笑场,未曾恢复盛年原样的嗓音、身段等。我觉得这是剧评作者的权利也是义务。
黄裳不肯服软的另一个原因,是因为他的这番自辩,针对的根本就不是梅兰芳,而是他的老上司、《文汇报》重量级的元老柯灵。
同样是已到风烛残年的柯灵,于1993年3月21日写作了《想起梅兰芳》。柯灵在文中重提黄裳的那篇《饯梅兰芳》,直截了当批评说:
这篇名文,清楚地表现出作者的才华,也鲜明地反映出作者的性格。当时此文很受赏识,似乎没有人想到这样对待梅兰芳是否公平,这样的强行送别是否过于霸道。
柯灵又说到在《饯梅兰芳》发表后,黄裳还有其他表现:
其实继《饯梅》之后,这位作家对梅放冷枪,就不止一处,例如说:“贤如梅博士,偶演《木兰从军》,武装扮一下赵云,虽然所谓梨园世家见多识广,也看不得,正如在台下梅博士说话一般,总有些不舒服。”原来不但在台上不行,连在台下说话也令人看不惯。甚至与梅毫无关联的题目,也要扫横一笔“孟小冬与梅兰芳的桃色新闻”。即使用最新式的精密仪器,大概也检验不出丝毫的善意来。
这就是前面所引黄裳自辩文中的“冷枪”的出处。柯、黄暮年剑拔弩张,与其说是为梅兰芳,不如说是缘自二人间之宿怨。稍后在香港披露出来的柯灵致古剑函即云:“我和黄裳的笔墨官司,事实极简单,内在原因,则可以说由于我深鄙其人。”暂且放下柯黄之争不论,回到他们争论的焦点《饯梅兰芳》一文。今天看来,黄裳所说内容未必不是真实的情况,写法上则未免不够厚道——当然,喜好京剧者历来有这个毛病,说话嘴损,喜欢阴阳怪气,这一点似是不好京剧的柯灵所难以了解到的。至于黄裳晚年的自辩,其既以资深剧评家自居,却说出“恢复盛年原样”这样的外行话,实在是够不上一个职业剧评家的见识,复何谈“这是剧评作者的权利也是义务”呢!
然而世事难料,大概是黄裳自己也未想到,在他发表《饯梅兰芳》文之后,其与梅兰芳不仅没闹翻脸,渊源反而愈结愈深。他居然能够神奇般地第三次在梅兰芳跟前闪出,而且成了梅兰芳最重要的著作《舞台生活四十年》的第一位责任编辑。
404 Not Found
- “四季童读·书香家风行动计划”启动
- “白玉壶中一片冰”——色彩学视域下的唐诗之
- 书房记
- 首个阅文书园将落地深圳
- 曾经是小孩
- 没有诸葛亮的蜀国为什么还能撑30年
- 以字词为媒 讲述中国故事
- 传承书院文化 书香浸润乡村
- 新书层出不穷,旧书为何仍然让人着迷
- 考古学者如何书写“餐桌上的微型史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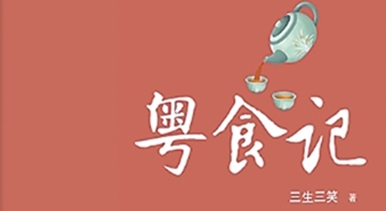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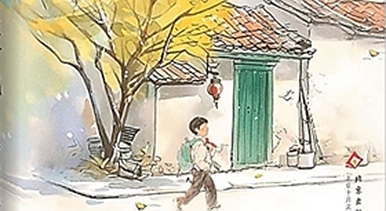






 京公网安备 11010102004843号
京公网安备 11010102004843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