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6年长篇小说:感应时代脉动 聚焦生活变异
发稿时间:2016-12-30 09:09:00 来源: 人民日报海外版
状写都市的新生气象
中国当下的都市,一直处于变动不居的扩张与膨胀之中。这种扩张与膨胀,既有市场的伸延,楼房的兴建,地界的扩大,更有务工者的进入,大学生的择业,就业者的流动,这种都市中的新兴群体的生活情状与生存现实,不同阶层人们的相互碰撞,不同向往的人们的相互竞争以及有得又有失的都市生活,有喜又有忧的都市故事,因为具有鲜明的时代特征,构成了当下中国故事最新的篇章。
王华的《花城》,写花村青年女性苕花、金钱草抱着改变命运的美好意愿进城务工,而花城这个城市不但冷若冰霜,而且固若金汤,使得她们只能蜗居于城市的边缘,生计与安全得不到保障,随之而来工作与爱恋,更是步履维艰。让人为之感动和纫佩的,是她们既没有轻易认命,也没有随意放弃,面对难熬的现实,人生原则必须坚守始终,这使她们艰窘的打工生计,既增添了几分额外的艰难,又内含了应有的尊严。
温亚军的《她们》,主人公是共同租住在京城一套公寓楼里的三个年轻女性,她们带着不同的经历、不同的向往,在这个相对狭小的空间里碰撞、交织、演绎。虽然“北漂”的生活时时处处充满着沉重感,如同雾霾一般的铺天盖地挤压着三个女性的青春活力,但她们却在以小博大、以柔克刚的人生努力中,尽力适应着都市的生活,并努力导引着自己的生命去除浮虚与迷离,向着本真与平淡回归。
焦冲的《旋转门》,由北京姑娘何小晗的人际交往与两性爱恋,作品渐渐展现出一个都市白领难以遂愿的的追求与并不顺遂的人生。作品从都市白领一族,透视了看似光鲜的人们背后的身心伤痛,同时又揭示了不安现状的人们左冲右突的人生追求。都市的丰繁,人性的斑斓,都于此一览无余地呈现出来。
捕捉历史的精神脉息
长篇小说中,有不少作品是写过往生活的,这或者是现代以来的百年历史,或者是过去不久的三五十年,这种或远或近的往事书写,虽非属历史题材,但却充满各具内涵的历史感。
2016年的长篇小说中,这种史事写作还表现出一个鲜明特征,这就是作家们不满足于依循传统的观念与写法,去诠释共识性的历史常识,而是以个人化的角度、个性化的视点,去着力揭示历史中的人文遗迹与精神脉息,以独特的人性蕴含与人情冷暖,让冰冷的历史复现其原本应有的温度。
方方的《软埋》由丁子桃和她的儿子吴青林两个人物,展开两条线索的叙事:丁子桃与吴家名两个苦命相怜的人结婚后,有了孩子吴青林,长大之后的青林由父亲生前留下的日记本和母亲失忆后的呓语,了解到母亲可能就是土改斗争中全家自杀的陆氏家族的逃生者。小说的另一个线索,是丁子桃痴呆之后,断断续续回忆起陆氏家族被批至全家自杀的整个过程。作者似乎是在引导读者去发现一段被掩埋和遮蔽的历史,在这一过程中,指向的却是人性自身。尤其是不断显现又最后彰显的“软埋”的残酷事实,更是托出了意味深长的一个意象性的概念:“软埋”。这便使这部作品的主题,超越了历史与文学,而具有一种伦理与哲理的深刻意义。
格非的《望春风》,以一个少年的视角状写一个村庄在时代发展中逐渐变化的全过程。在“我”的眼里,村子里的人们既有着这千丝万缕的人际关系,又因为这些人际关系而在某种方面达到了微妙的平衡和内部和谐,在外界因“文革”而翻天覆地时,村子里却因为村领导的种种善意而让大家较为平稳地度过了这段极端年代。一个村子总能守住各种秘密,源于每个人物都有自己的道德标杆和行事法则,他们的愿望,只是在村子里默默度过一生。行云流水的叙事,波澜不惊的故事,都在自然而然地展示江南农村特有的民俗风情,自有的内在秩序。
路内的《慈悲》,由普通工人水生的人生经历,讲述了一个国营工厂在蜕变中经历的种种窘境,为了得到为数不多的补助,人们各显其能,不择手段,弄得人际关系格外紧张。而在时代更替之后,市场经济在带来新的活力的同时,也带来新的社会问题,如水生这样的普通工人,只能以深怀慈悲的隐忍,回望过去和面对现状。个人化的故事背后,有时代的浓重身影,更有情怀的坚韧持守。
2016年值得关注的长篇小说,还有很多,这是主要从现实题材和写实角度所做的观察,难免挂一漏万。但由这样一个简要的描述可以看出,我们的作家,无论是名家,还是新秀,都有不负时代的坚定追求,都有不负自己的卓越表现,这种文学主体精神的凸显与高扬,应该是比作品本身更让人为之兴欣和鼓舞的事情。白 烨
404 Not Found
- 《微相入:妙手修古书》——我在图书馆修古籍
- 散文《远去的渔火》传统与现代的交织
- 一场不停歇的“再书写”
- 我人生最开始的好朋友:拥抱生命的温暖与力量
- 书窗叠影
- 《我的母亲做保洁》——让劳动的价值被看见
- 首次实现京城东南西北联动,书市人数再创新高
- 读《粤食记》——美食,省不下来的庖厨功夫
- 今天,更需要深度阅读
- 青山不负赤子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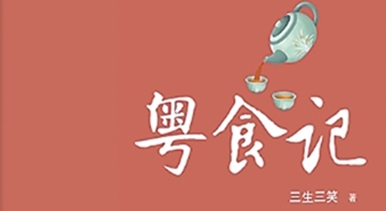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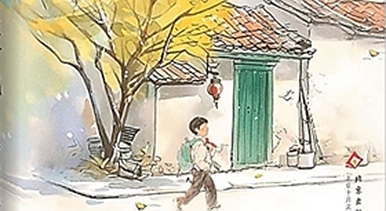








 京公网安备 11010102004843号
京公网安备 11010102004843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