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何时回首谢红尘》
发稿时间:2017-09-11 11:09:00 来源:中国青年网
我之所以做出这个决定是经过认真考虑的。
首先,董浩云是一位非常值得研究的历史人物。他白手起家,与时俱进,特别是自20世纪50年代后,他以香港为基地,抓住航运业几次发展的机遇,旗下船队的数量迅速扩张,本人更跻身世界船王,因而具有一个成功企业家的特点与个性。而他对事业的追求、为国家争光的理想、对艺术的热爱以及对推动海上教育的热诚,一般企业家更是难以企及:在航运界和海外华人世界中,他的创业以及为航运事业作出的贡献可谓声名显赫,而董浩云在国际交往及两岸关系上的作用,亦非他人所能比拟。
其次,董浩云的生平不仅值得研究,而且有必要研究。过去内地与外界封闭,对于董浩云的事迹几乎无人知晓;改革开放后,由于董浩云长期以来与台湾政经各界具有密切的交往,在当时两岸敌对的状态之下,他不可能回大陆投资探亲。而且他去世的时间也比较早,因此内地民众只知道香港有个船王叫包玉刚,直到董建华出任香港特别行政区首任行政长官时,人们才知道他的父亲也是一位世界船王,但对他的生平和历史地位仍知之甚少。以往坊间只有一部董浩云的传记,那是香港回归前董建华已确定为特首,有作者抢先写作,但其内容多为道听途说,既未采访调查,更未查阅相关资料,存在许多错误,与一部真实可信的人物传记尚存在很大的距离。
第三,对董浩云的生平目前业已具备研究的条件。多年来在编注日记的过程中,我对董浩云的一生已经有了初步的认识,更重要的是,在编注日记的同时,我已开始注意收集各方面的数据,并与传主亲属建立了良好的关系,彼此之间相互信任,他们不仅同意接受我的采访,而且还将董浩云生前收集的全部资料对我开放,这对我日后的研究具有关键性的作用。
我是一名历史学者,长期从事档案的编辑和研究工作,在进行任何一项研究之前,首先注重的就是史料的收集。因此在决定撰写董浩云生平活动之前,我即开始进行各种数据的收集。这些年我在收集民国史档案的同时,也注意收集与董浩云相关的史料,先后从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以及董浩云曾经活动过的地区如上海和天津的档案馆中收集到一些他早年工作的资料,另外,台湾“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档案馆以及“国史馆”,还有美国斯坦福大学胡佛研究所等机构,也保存部分相关资料,我都尽可能加以收集。
我还注意查阅相关的报刊,特别是董浩云亲自创办的《航运》杂志共500多期,它详细地记录了20世纪50-80年代中国和世界远洋航运事业的成长和发展;此外,董浩云先后斥资出版了四辑董氏航运丛书,他平时还经常撰写文章或发表演讲,接受报刊的采访,中外许多报刊亦热衷对他加以报导,这些都是了解董浩云生平以及他的航运事业发展的重要数据。
在收集文字数据的同时,我还对董浩云的亲友及部属进行有计划的采访,事先准备好采访要点,有备而来,收获很大。这里需要特别提出的是,董浩云的长女董建平多年前已经开始进行这方面的工作,先后访问了数十位董浩云的故旧,从而抢救出大批史料,对我的撰写极具帮助。
在撰写本书的过程中,我还阅读相关著作,特别需要补充有关远洋航运方面的知识,同时还要了解战后国际关系中的发展与演变,特别是对于航运影响重大的事件,如朝鲜战争、越南战争,苏伊士运河危机、中东战争以及能源危机等,因为这些都与董浩云生活的时代以及事业的发展密切相关。
日记是作者记录自己一生最生动、最可靠的数据,然而最初在编注董浩云日记的过程时,由于我对传主不太熟悉,对他身处的环境以及周围的人物也不大了解,而日记的文字十分简单,内容又相当隐晦,因此对许多事情的原委感到模糊不清,似懂非懂。随着史料的不断发掘和占有,在写作过程中我再多次重新认真阅读日记,这样就会对传主一生的活动及其志向产生一种全新的认识。
对我来说,撰写董浩云的传记最重要的收获是能够亲自查阅董浩云的文件,包括公司及个人的各种数据。董浩云生前特别重视各种资料的收集和保管,这些数据报括各个时期的公司报告、来往文件,会议记录以及私人书信和各类剪报等等,并经过初步整理。虽然目前还比较散乱,但却为研究董浩云的生平奠定了重要的基础,更重要的是,这些资料董氏家族对我全部开放,使我对了解董浩云生平活动以及旗下事业的发展历史有了一个全面而直观的认识。
因为我还有其他研究课题和教学任务,收集史料经历了一个漫长的时间,但这是撰写传记的基础。在数据大致收集后,便开始进行整理、分析、爬梳和比较,并在此基础上作些写作前的准备,譬如先行编撰董浩云年表,配合出版《董浩云日记》与《董浩云的世界》(繁体,2004年11月,香港中文大学出版社:简体,2007年7月,北京三联书店),相继在香港和北京举办新书发布会,产生一定影响。2007年9月于董浩云诞辰95周年之际,上海交通大学召开会议予以纪念,我受董氏家属的委托,事先邀请各界专家撰写论文,并于会议开幕的同时出版专书《董浩云:中国现代航运先驱》,引起社会各界对董浩云研究的兴趣。与此同时,我还建议天津档案馆编辑出版《董浩云在天津》档案数据汇编,这样就为董浩云早年在天津的活动提供了大量史料。
在此期间,我曾根据董浩云一生中所经历的重大事件,先后撰写了十余篇学术论文,提交学术会议,争取得到学界的批评和意见,以供写作中不断修改。这些论文先后已经出版,并成为本书的基本架构。
2015年6月,拙著《董浩云与中国远洋航运》由香港中华书局出版,该书50余万字,对董浩云的生平和航运事业的发展进行了全面的介绍,得到学界的认可。其后又承蒙北京新星出版社同意出版该书的简体版,这是对我最大的鼓励和支持。根据出版社的要求,我又对原作进行了较大幅度的删减,并将书名定为《何时回首谢红尘:董浩云传》,“何时回首谢红尘”是1947年11月董浩云在病榻上听到旗下「天龙」轮横渡大洋的喜讯,兴奋至极而写下的四首七绝诗中的一句,也是现存董浩云日记最初的文字。我想以此诗作为书名,可以充分表现出他对国家民族的那份感情眷恋、对航运事业的那种执着追求。
董浩云成长于大陆,成功于香港,事业发展于全球,旗下船队遍于全世界,是一位享誉世界的船王,然而董浩云又不是一个单纯以追求利润为目的的商人,他具有远大的理想和宏伟的目标。董浩云虽然长期生活在海外,但他始终没有忘记他是一个中国人,总是将他事业的发展与国家的强盛联系在一起,而且他一直都在为实现这一目标而奋斗。董浩云在1967年元旦的日记中回顾一年中所取得的成绩之后曾自豪地说:「艰辛必多,收获亦大,愿为国人航运史开一纪元。」因此本书必须反映出他的这种志气与抱负,不能只是将他简单地视为一个成功的商人,也不应仅就其个人的生平予以论述,而是应将他与整个国家的强大、现代远洋航运事业的发展联系在一起,希望通过叙述董浩云传奇的一生,让读者了解中国近代航运业如何从无到有、从小到大的发展过程,了解董浩云等这一批老一辈企业家为了达到这一目的所作出的奋斗和努力。
404 Not Found
- 让中国艺术史可视可感
- 在文字与自然间独自探寻身心灵的融合
- 东坡的清明
- 一版三形式 承继与开新
- 又是繁花满枝时
- 学术伉俪 文章知己
- 文人画的再发现:在人工智能语境下
- 思念的那头
- 清明为何适宜放风筝
- 良训传家:中国文化的根基与传承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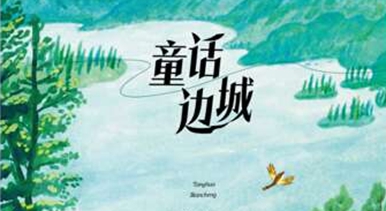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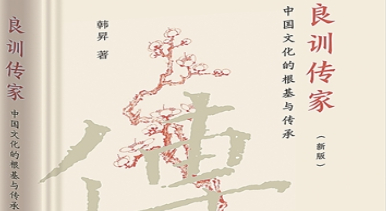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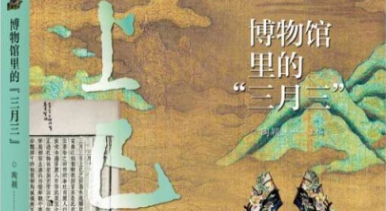






 京公网安备 11010102004843号
京公网安备 11010102004843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