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空间诗学》
发稿时间:2016-12-08 11:20:00 来源:中国青年网

书名:《空间诗学》
作者:[法]加斯东·巴什拉
译者:龚卓军 王静慧
出版社:世界图书出版公司
出版时间:2017年1月
定价:48.00
书号:978-7--5192-0772-4
导读:空间原型的
阅读现象学
龚卓军
其实不只是巴什拉的作品难懂。我曾经读到某些小说的某些段落,明明描写着具体的空间,却令人产生一种无以名之的迷惑激动感。
譬如,村上春树的《下午最后一片草坪》。
主角是个大学生,夏天帮某家公司割草打工。小说的后半段,他在最后一个工作日,下午两点三十五分,在业者指定的最后一片草坪上细心地割完草后,草坪的女主人邀他进屋内喝点冷饮。
女主人头也不回,引他进入室内,“从夏天午后阳光的洪水里突然进入室内,眼睑深处扎扎地痛,屋子里像用水溶化过似的飘浮着淡淡的阴影,好像从几十年前就开始在这里住定了似的阴影,并不怎么特别暗,只是淡淡的暗”。从阳光下进入家室内,好像进入了时间的长廊。“走廊装有几扇窗,但光线被邻家的石墙和长得过高的榉树枝叶遮住了。走廊有各种气味,每一种气味都似曾相识,这是时间生出来的气味……旧衣服、旧家具、旧书、旧生活的气味。”
上楼梯时,旧地板发出咯吱咯吱的声音。在二楼重见的光线中,女主人拿钥匙打开了绿漆已渐褪色的门把锁。
“房间是典型十几岁少女的房间,临窗放着书桌。另一边是一张木制小床,床上铺着没一点皱纹的珊瑚蓝床单,放着同色的枕头,脚下叠着一条毛毯。床旁边是衣橱和化妆台,化妆台上排着几种化妆品,还有梳子、小剪刀、口红和粉盒之类的东西。看起来并不像特别热衷于化妆的那一型。
“书桌上有笔记和字典,法语字典和英语字典,好像用得很勤的样子,而且不像是胡乱翻,是细心翻过的样子。笔盘上该有的笔类都一应俱全地齐头排着。橡皮擦只有一边是磨圆的。其他就是闹钟、台灯和玻璃纸镇,样样都是朴素的东西……定做的书架上摆着各种书。有文学全集、诗集、电影杂志、画展的说明书。英文平装书也有好几本。”
接下来,这位死了丈夫、未说明女儿下落的女主人一边喝着玻璃杯里的伏特加加冰块,一边要求大学生打开衣橱。“衣橱里满满地挂着衣服,一半是洋装,另一半是裙、衬衫、外套之类,全部都是夏天的东西。有旧的,也有几乎没穿过的。裙子大部分是迷你裙。趣味和质地都不错,虽然不是特别吸引人,不过感觉非常好。有了这么多衣服,整个夏天约会都足够换着穿了。”
最后,她要求他再把抽屉拉开看看。“我有点迷惑不解,不过还是干脆把衣橱上的抽屉一个一个拉开来看。在一个女孩子本人不在的房间里,这样翻箱倒柜地乱翻——就算得到她母亲的许可——总觉得不是一件正当的行为。不过拂逆她也嫌麻烦,这种从早上十一点就开始喝酒的人,到底在想什么,我也搞不清楚。最上面的大抽屉里放着牛仔裤、运动衫和T 恤。洗过,折得整整齐齐,没有一点皱纹。第二格放皮包、皮带、手帕、手镯,还有几顶布帽子。第三格放有内衣和袜子,一切都那么清洁而整齐。我忽然没来由地悲伤起来,觉得心头沉甸甸的。然后我把抽屉关上。”
为什么会有这股没来由的悲伤呢?整齐的抽屉、夏季的衣橱、案头的法语字典、女孩不在的房间、绿漆泛白的门锁、木板吱呀的楼梯、充满旧时光气味的走廊、阴暗的家屋,以及早上十一点就开始喝酒的女主人。小说家通过这些家屋意象的描写,将读者的想象引向何方呢?答案似乎并不明显。作为读者的我们只是感受到了一种氛围,这种氛围让读者暂时忘了阅读,让读者内在暗涌,陷入切身的想象中。这种氛围甚至让读者不禁放下手中的小说,恍惚之间,神思已走向一个亲人的房间,一位已不在场的亲人的房间。
阅读中的回荡现象
当我们在阅读中遭遇到一个清新的意象时,受其感染,禁不住白日想象,依恃它另眼看待现实生活。这种没来由的激动与另一类眼光的萌生,这种不能以因果关系解释的阅读心理现象,便是《空间诗学》的阅读现象学起点,巴什拉称之为“回荡”。
一般来说,我们比较常经验到的阅读现象是共鸣而不是回荡。从巴什拉的观点来看,对于某个意象所产生的共鸣,比较接近精神上的奔放状态,也接近知性上的联想,而不是存在上的整体震撼。当我们经过某种意象的冲击,而引发出一种存在上的改变,“就好像诗人的存在就是我们的存在”,这时,诗歌和意象就彻底占领了我们,深深打动了我们的灵魂,让我们感动。于是,我们处在回荡的震撼之中,依据自己的存在处境而诉说诗意。我们会以为自己体验过这种诗意,甚至以为自己创造过这种诗意“有了这种深切的感动之后,所谓的共鸣才会接着出现,在发生共鸣和情感的反响之中,我们的过去被唤醒,我们把自己过去的相关经验跟小说和诗歌意象所呈现的情境相对照,于是我们在精神上掌握了某种意象的典型特质,在知性上发现这些特质其实潜存在我们过去的许多生活体验中。
就此而言,我们可以很清楚地看到,巴什拉从现象学观点反对一般的文学心理学和精神分析文学理论的批评方法。从他的现象学心理学来看,他最关心的是读者的心理学,其次是作者的心理学。可以说,他的现象学心理学的文学观点奠基于下面这一句话:“如果我们要确切点出意象的现象学究竟所指为何,如果我们要确切说明发生在思维之前的意象,那么我们要说,诗意不仅是精神(或心智)的现象学,更是灵魂的现象学。”对巴什拉来说,每一个心灵都同时由精神和灵魂所组成,而精神(或心智)跟意象的现象学毫无关联,因为心智属于心灵的客观层面,而意象则属于主体层面。意象的发生场域是在灵魂的活动中,它先于思维出现。思维和理性在人的精神层面运作,其作用是将现实加以客观化,这种客观化运用的是概念和隐喻,而不是意象。
对于诗歌来说,隐喻没有现象学研究的价值,它们只是理智化了的意象:“隐喻是一种伪意象,没有深切、实在与现实的根源,隐喻是一个转瞬即逝的表达方式。它是……用过一次后就死去的东西。”由于隐喻限于其理智化、过度现实、强调因果关联,因而隐喻所使用的字词变得过于静态。如果我们拿隐喻来作为我们了解现实的参考点,那么隐喻就会限制我们所要了解的事物,让它变成一个思考上固定而静态的概念。而灵魂强调的却不是客观性,而是主体性。灵魂属于想象的机能,它运用的是意象的力量,这些意象的力量要发生作用,当然不是在我们日常的意识生活中,而是在思想发生之前的意象想象活动中。
404 Not Found
- 乡村希望书屋有了“模拟联合国”
- 诗人们在讨论:AI时代,如何写好一首有心跳的
- “阅读北京,京彩书香”主题研讨会在京举办
- 重庆“弃书库”:本店无新书 店内皆同学
- 武汉:从地铁到游船,阅读融入日常
- 《假装被风儿吹走了》带你走进初中生的世界
- 晋博推出古籍专题展 在书香中追寻先贤印记
- 北京书市为数千古籍旧书找“新家”
- 《南方巴赫》:南方文学的青春书写与创作实验
- 阅读:拯救那些无法言说的经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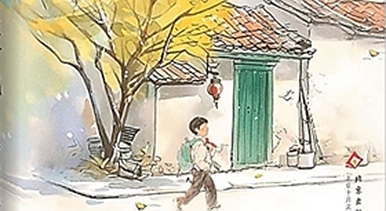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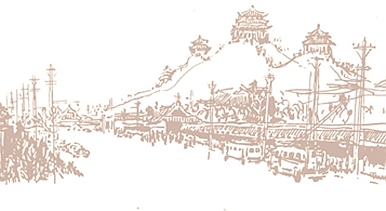







 京公网安备 11010102004843号
京公网安备 11010102004843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