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心武专访:我在文学领域种了四棵书
发稿时间:2016-04-22 11:19:00 来源:中国青年网

日前,著名作家、茅盾文学奖获得者、红学研究家刘心武的最新文集《刘心武文粹》正式出版。这套《文粹》由译林出版社联合北京凤凰壹力共同推出,涵盖刘心武在小说、散文、红学研究等各个领域的优秀作品,共有26卷,已在近期陆续上市。记者就文学创作等话题对刘心武进行了专访。
记者:很多人拜读您的第一部作品都是《班主任》,这是您的处女作吗?
刘心武:我算是一个贯穿型的写作者,一个马拉松长跑式的写作者。之前我到河北师范大学做了一次演讲,谈关于我的写作,有人就提出了这样的问题,说刘老师您是不是能谈一谈你的处女作《班主任》的写作发表过程。
首先这个问题有误,《班主任》这篇小说并不是我的处女作,我的处女作是1958年发表在《读书杂志》上的一篇文章,《班主任》是发表于1977年,间隔很久了。而在《班主任》之前,我已经有整本书出版过。所以《班主任》算是我的成名作,而非处女作,这也说明我的写作史是很长的。
记者:刘老师在文坛的地位不言自明,您的粉丝中大部分是有人生阅历,年纪偏大的读者,对于读者的年龄偏向您怎么看?
刘心武:在《班主任》发表之后,我又经历过很多的写作阶段,一直延续到今天。那时和我一起写作的人,有的因为种种原因,退出了文坛,或者淡出了写作的行当,可是我一直坚持下来了。所以这样说来,我的读者群还是比较大的,而且囊括的年代群也比较多。
举几个例子。一个是大概在80年代末,那个时候人民文学出版社有自己的专卖店,在新街口。因为人民出版社出版过我的一些书,所以进去看了看。店里有一位年龄比我略小的妇女,看到我很兴奋,立刻就来招呼我,我就知道她是我的一个读者。她买了好几本书要我签名,还叫过来一个上中学的姑娘,她说:“这是我的女儿,我读了你的书之后,我很喜欢。现在虽然很多文化潮流风起云涌,出现了新的作家,但是我还是推荐我的女儿来读你的书。”对此我很感动。
因为那个时候我已经开始边缘化了,读者群不是囊括所有年龄段的。我的同龄人中有一部分是我的读者。后来的60后、70后的朋友要读新锐作家的作品,他们不一定都热衷于我的作品,这其中我的读者不算很多。这个例子说明有一些老的读者,开始把我的作品推荐给他的下一代,这给我的印象很深,我很欣慰。一位母亲读了我的作品,她很喜欢,她觉得自己的女儿也应该继续读。所以我还得继续产生新的作品。
记者:您刚才谈到的边缘化具体是指什么?是如何应对的?
刘心武:在80年代的时候,打开门户以后,西方现代派、后现代派,大量文学潮流的涌入,也带来了很多新的写作技法,比如说荒诞的写法、变形的写法、时空交错的写法、意识流的写法等等。在这种情况下,像我一样写实主义的作家处境并不是非常好,因为显得有点落伍。所以我想是否该给自己重新定位,于是我努力去阅读一些西方现代、后现代的作品,也尝试用这些手法写过一些作品——在我的《刘心武文粹》里,有一些这方面的成功的尝试,比如《无尽的长廊》,就是一个很有趣的小长篇。
还有一些短篇比如像《贼》,《洗手》也都是在魔幻、荒诞、变形这方面去揣摩,利用这些手法来完成自己的写作心愿。但是绕了一圈以后,我给自己的定位还是我最得心应手的写实的手法。
在我给自己定位的过程中间,还有一个有趣的经历。1998年我去美国,在纽约唐人街有一个比较大的中文书店。店主很热情地接待我,说店里在卖我的书。我问销量怎么样?他说你的书卖得不是最好的,最好的是50年代出来的作家。这很正常。
我告诉他我在考虑怎么调整自己的写作,我是不是要像他们那样去写。正在我们讨论这个问题的时候,店里进来了一位女士,大概比我要小个十几岁。最初她没有注意到我,后来和我面对面的时候问我,是你吗?我就知道她是我的一个老读者。我说,对,是我。尽在不言中。我突然很惭愧地说,你可能只记得我的《班主任》,还有一些很浅陋的,比如《爱情的位置》,《醒来吧,弟弟》这样的作品。我说现在我也觉得这些作品,是一些很笨拙的文字,可能在当时起到一定的开拓作用,我在调整自己的写作方略,想写出更好的作品。
这时她突然她瞪着我生气了,而且双眼蓄满了泪水,她觉得难为情地扭过头去。我觉得很奇怪,店主也很惊讶,那个时候我太太也在,问这位女士怎么了。然后她忍住眼泪,正过头来说:“你不要这样说,你那些作品就是我的青春。”说完她就扭头离开了书店。我没来得及留下她的姓名。
这给了我很大的鼓舞。如果沿着自己的写作路数继续往下走,我应该吸纳各种各样的文化营养,包括现代主义和后现代主义的文化营养。那个时候我对西方一些新的文论很重视,比如结构主义、解构主义、女权批评和新批评等。这些营养我都要吸收,但是到头来,我应该还是我,我最拿手的应该还是写实主义。
这些老读者给我的鼓舞,令我永远难忘。我很后悔那时没追出去。
记者:她认为你否定自己的写作风格就等同于否定她的青春。
刘心武:她说你别把这段阅读史给否定掉。这对我来说很珍贵的。另外我很欣慰的是,在后来有一段比较边缘化的情况下,我将写作坚持下来了。
记者:您所坚持的写实主义得到了您所期望的社会回应吗?
刘心武:在80年代的时候,一些作家尝试魔幻、变形、荒诞、现代派的写作风格,我尝试超级现实主义,比写实还写实,写纪实小说,引起了轰动。其中《5·19长镜头》写的是1985年在工体中国队和香港队的比赛,所有人都觉得中国队会赢,没想到中国队输了,出局了,引发中国足球史上第一次球迷闹事事件,引动《人民日报》都发表了评论员文章。
怎么解读球迷闹事的现象?我带着这个问题采访了被拘留的闹事者、体委官员和新闻记者,写成纪实小说《5·19长镜头》。
当时我的解读和官方有一些差别,官方当时对我也很容纳,认为我的解释是对社会心理进行了梳理,所以也纷纷转载这篇作品。但悲催的是,中国足球不争气,一到国际重要赛事老输,所以《5·19长镜头》老有人重新提出来,包括中央电视台的体育频道,一些很年轻的评论员或者主持人,他们在交谈时也经常提到,使这个作品一直流传到今天。有些年轻人想一探究竟,可以到《刘心武文粹》里找到这篇作品。这也是我认为值得纪念的,有英文版的,流传比较广的一个作品。
记者:据我所知您写的《公共汽车咏叹调》也是一个纪实小说,和《王府井万花筒》构成三部曲,都十分轰动。但最著名的当属《钟鼓楼》,听说这部小说您采取了比较独特的写作结构?
刘心武:我的第一篇长篇小说就是《钟鼓楼》,得了茅盾文学奖。《钟鼓楼》写的是北京的世俗生活,牵扯到很多的人物以及他们的前史,即在故事发生阶段之前这个人的命运。这部作品巧妙在结构上,整个故事开始是在1982年的12月12号早上7点,故事结尾是在这一天的晚上7点,12个小时在一个钟鼓楼下的小杂院,浓缩了很多人生百态。
这个结构到目前为止,我觉得还是具有独创性的,叫做橘瓣式。一般的长篇小说都是线性叙述,根据时间叙述;或者串珠式,每一个重要的情节都是一个珠子,用一根主线串起来。还有阶梯式,不断递进引向高潮,文本策略上让你越看越过瘾。另有屏风式,完全靠悬念抓人。大家知道从结构主义学说来说,所有的破案小说无非是两个模式,一个是谁是凶手不告诉你,结果你觉得每一个人都像凶手。到最后揭晓的就是你最没怀疑的那个人,他反而是凶手,你所怀疑的人最后都不是凶手。另外一种,一开始就告诉你谁是凶手,但他总是逃脱,总是揭露不了,到最后才能把他抓住,这也是屏风式的一种结构。《钟鼓楼》就抛弃了所有的这些结构,做成了一个橘子,把橘子皮剥开之后,里面是抱团的橘子瓣,每一瓣是独立的,有滋有味,这一瓣里面有他的人生,他的故事,他的前史,他当下的状况。但这只是一瓣,又有一瓣,又有一瓣,最后这些橘瓣合起来,又很紧凑,构成一个小说。
所以《班主任》之后,《钟鼓楼》应该是我的文学创作一个真正的成果,因为在《班主任》中,我只是用小说的形式来抒发自己内心对社会的一些看法,起到一些振聋发聩的作用,在文本上没有新策略,甚至在“四人帮”时期的文本策略,也还在沿用。所以《班主任》只是一个内容革新的觉醒,《钟鼓楼》是文本策略的觉醒。
文学要回归文学本身,这个过程也是要过渡的,比如说短篇小说《我爱每一片绿叶》,就开始完全从社会学的角度,转到人性探索;中篇小说《如意》在1982年拍成一部彩色电影,现在从网上可以找出来看,是一个文艺片,手法是比较小众化,如果没有一定的文艺滋养的话,可能看起来觉得比较闷,但实际上影片是很抒情的,弘扬了人道主义。
这个电影最早被台湾人重视。侯孝贤看了以后很吃惊——大陆作家也能把人道主义表现得如此充分,大陆导演黄健中也能把这样的题材诠释得那么好。那是80年代初,后来台湾出了一部《世界电影经典》,很多大陆的东西都没有收录,偏偏收了《如意》,这是一个很有趣的文艺现象。

记者:所以您的新书中也收录了一些自己满意的中短篇。
刘心武:从《班主任》到《我爱每一片绿叶》,到《如意》,一直到《钟鼓楼》,还有中篇《立体交叉桥》,这些精华都存在于凤凰壹力通过译林出版社出版的这套《刘心武文粹》里。
记者:您之前出版过文集、文存,这次的《刘心武文粹》有什么特别的亮点?这三者有何不同?
刘心武:文集就是一个作家作品多了以后,集中展示一下,没有什么历史方面和作者整体评价方面的考虑,比如1993年我在华艺出版社出版的《刘心武文集》8卷。
2012年江苏人民出版社出版了《刘心武文存》,文存就是有文必录,只要是公开发表过的作品,不论是失败的、幼稚的、糟糕的还是难为情的作品,既然公开发表了,就不能回避。像我这样的马拉松长跑型作家,我认为自己没有很高的文学价值,但是从1958直到2016年依旧在发表作品,是有历史的价值的。
而文粹就是只选好的,我自己觉得失败的、幼稚的、糟糕的,不值得向读者推荐去读。这其中收入的都有可读性,除了小说以外,还有我的《红楼梦》研究。
记者:那这部文粹中有收录您在2016年的新作吗?
刘心武: 2016年《书屋》杂志的第一期,刊登了我最新的文章《<金瓶梅>中的男体描写》。我就把这篇文章补充到了《刘心武文粹》中,在《从<金瓶梅>说开去》这一卷。
作为一个文学长跑者,有时候需要把自己作为一个个案,提供给文学史的研究者研究——在中国现代文学的发展过程中,他是怎么过来的,这个人当初多么幼稚可笑,写的东西多么糟糕,但是他又引起了轰动,作品又很有争议。有些作品现在看来还有一定的比较久远的审美价值,虽然很杂驳,但是要做一个罗列,这就是文存的意义。
记者:许多作家都十分推崇多读外国的文学作品,您认为是国内还是国外的文学作品对您的写作更有所助益?
刘心武:我在文坛这么多年,也有酸辛的一面。社会上确认一个作家或者作品的价值,也需要看社会坐标,这是不可避免的,比如是否获奖?是不是有名?正是因为《钟鼓楼》得了茅盾文学奖,所以大学里面讲当代文学,会讲到这个作品,因为是一个得奖的作品,被一个社会评价坐标肯定过。
我始终认为到目前为止,我最好的长篇是《四牌楼》,我非常珍爱这部作品。法国汉学家跟我商量,翻译这部作品。但是《四牌楼》篇幅很宏大,中文翻译成拉丁文要增加很多篇幅,所以他们选择中间《蓝夜叉》这部分翻译成法文,效果很好,所以还是有知音。
2014年出版了最新的长篇小说《飘窗》。我在后来的长篇小说写作过程当中,不断地从各方面吸取营养,主要是通过翻译,来领略外国作品的风采,除了西方的,也包括日文小说。我西文水平还不能直接阅读外文的原版,那么还是从自己的民族经典当中汲取营养。所以当时重点读两部,一部是《红楼梦》,一部是《金瓶梅》。
记者:大部分年轻的朋友熟悉您都是通过《百家讲坛》,当时出于什么考虑想参与这档节目?
刘心武:我解读的红楼梦通过《百家讲坛》的系列讲座,引起了轰动。吸引了80后、90后这一批年轻的读者,这个有人很惊讶。有人说这个人怎么回事,他能够在70年代末、80年代引起过轰动,又在21世纪初引起过轰动,这是很不容易的,因为这是两个审美趣味、阅读趣味完全不同的历史时期,人也不一样了。我就不细说怎么引起轰动,引起轰动的原因是什么。但是总而言之,80后、90后一些通过看我《红楼梦》讲座以后,说这人值得注意。什么“人就是想出名,所以来讲《红梦楼》”,后来一查资料,因为从百度很容易百度出我的资料,这个人早就出名了,他用不着靠这个出名,1977年他就出名了,1977年,2007年你想多少年?我《百家讲坛》引起轰动的节点,应该是2005年-2007年-2010年,老早就出名了,他凭什么出名?原来他还有《班主任》,还有《钟鼓楼》,找找看看怎么样。结果我就发现像你说的,一些很年轻的人,包括你说的已经出了名的人,他觉得读起来很有趣。我感觉到很欣慰,但是他们不明白在哪里呢,不明白我讲《红楼梦》,并不是为了通过《红楼梦》来营造自己新的价值,我当时就是为了读《红楼梦》,向《红楼梦》取经,看看我们的前人用方块字怎么写好小说的,我能从中得到什么营养,我怎么写好我的小说,我从这个角度切入的研究的《红楼梦》。
记者:其实在您后续的写作中,也能发现一些细节是有《红楼梦》和《金瓶梅》的影子,所以也是在传统文学中有所借鉴对吗?
刘心武:像我说我自己最喜欢的小说是《四牌楼》,《四牌楼》里面浸润了《红楼梦》的营养汁液。如果知道我为什么讲《红楼梦》,再读《四牌楼》就能感觉到。当然《四牌楼》也有很多新的手法,比如说在写《四牌楼》之前,高行健还没有出国,我们俩是密友,经常在一起讨论方略。
那时我们就说一部长篇小说,能不能够用三种人称叙述交错。用第三人称“他”和第一人称自传性的向读者叙述都不稀奇。关键是第二人称“你”如何使用?后来他写了他的第一篇长篇小说《灵山》,我也写出了《四牌楼》,都是三种人称交错的手法。
但是《红楼梦》的精髓在于让你懂得珍惜青春,珍惜生命。生命是短暂的,青春像花朵一样,很快会谢落。《红楼梦》的贾宝玉希望那些女孩子永远不要出嫁,永远像鲜花一样开放着。他以为女儿是水做的骨肉,男人是泥做的骨肉。《四牌楼》里面写的一系列上世纪的青春女性,用三种人称交叉叙述她们的命运,无限的悲悯和感慨,希望这些花朵不要陨落,写了一个世纪的动荡和对个体生命的影响,这就是受《红楼梦》的影响。
《金瓶梅》基本是冷叙述,硬心肠。它写人的命运很冷,死者自死,活者自活,死了就死了,活着继续活,有点没心没肺,而且看起来无是无非,写人性恶写到刻骨铭心的地步,但是它没有批判。《金瓶梅》的这种叙述在《飘窗》里有所体现,写人与人之间的冷酷、无情,不动声色,是受《金瓶梅》的影响。我从中国的方块字的小说里面,汲取了很多营养,运用在我的小说当中。
记者:《刘心武文粹》中有那些内容是最令您印象深刻的,可以简单和大家讲讲吗?
刘心武:我在1958年发了第一篇稿子,那个时候我才16岁,当时的政治风浪卷不到我,另外我也不是知青下乡的那一代人,留在了城里。文化大革命后期,要求恢复一些文艺的生产,就开始恢复《人民文学》杂志和诗刊,当时知青还没回城,王蒙他们还没有改正,我当时却能够投稿,能够写作。
在“四人帮”当政时期,要按照“四人帮”的文艺技法来写作,比如“三突出”,就是在所有的人物当中要突出正面人物,在正面人物当中要突出英雄人物,在英雄人物当中要突出主要英雄人物。“样板戏”都是这么来制作的,像汪曾祺执笔的《沙家浜》,就是成功运用“三突出”的例子,但是越写越窄,最后大家都写“三突出”。
当时丁玲来到北京,想要平反。我那时候在北京出版社文学编辑室做编辑,去找她约稿。我记得很清楚,这个老太太有棱角,斜眼看我。我说读者们期待你的文章出现,我们出版社现在组建一个双月刊叫做《十月》,先以丛书名义出,可以给你发表。她拉开桌子旁的一个抽屉,只拉了一半,问我说你能发表?我说能发表。那个时候,我因为《班主任》已经有点名气了,出版社很看重我,我是《十月》领导小组成员之一,有一定的决定权。
她彻底把抽屉拉开,拿出一沓稿子给我,说你拿去看看,这可是退稿。我当时很高兴,觉得老太太不一般。当时我和妻子儿子住在一个11平的小平房里。连夜看了丁玲的稿子以后,觉得这个人真的很不容易。
临走的时候她告诉我退稿是因为编辑让她改结尾部分。我看了以后觉得稿子一气呵成不能改,就给她写了一封信,说我认为结尾很好,不用改,我们完全可以发表。她很高兴。我就排进了《十月》里的一期。
没过多久,有一天家门口听到喧闹,出去一看,车上下来当时刚刚恢复了作家协会书记身份的葛洛,问我说丁玲是不是有一篇文章在你这?我说是,在我这。
他说中央下了文,给丁玲平反,她需要在《人民文学》杂志亮相。葛洛当时负责《人民文学》杂志,这个文章应该由《人民文学》发表。我说不行,已经在《十月》排了,马上要下厂。但他一本正经地说,中国的文学和政治联系得很紧密,平反以后她在哪亮相很关键,中央让她在《人民文学》杂志亮相。我很为难,说《十月》杂志也不是我一个人负责的,我们还有领导。他说这些你不用负责,我们来搞定,现在把文章交给我就好。
然后我们就准备回编辑室,车刚开到出版社门口,又来了一辆小汽车。当时坐小桥车的人都是干部。车上下来的是严文井,严老说丁玲平反了,她的文章在《人民文学》杂志发表的同时,要立即收进我们人民文学出版社给丁玲出的集子,剩下的你别担心,第二天我们跟北京市委联系。我经历了类似这样的事情,都收录在《刘心武文粹》里,非常地独家有趣。
而且大家知道,丁玲后来和中国杂志协会的关系是很紧张的,并不和谐。当时中国作家协会有一些人对我很好,我又是中国作家协会一些人培养出来的,觉得很为难。丁玲在有一次公开讲话抨击作协的时候,忽然把我摘出来,说刘心武不错,跟我写过信。他们退我的稿,可是刘心武给我写信,他支持我的这篇文章。丁玲的家属在她去世以后,找到了我写给她的那两封信,公布在杂志上。正好我也收录到了《刘心武文粹》里面,大家可以看一看,当时文坛上的新老作家是怎么交往的。
记者:之前您说自己种了四棵树,还说要把树上结出的果子给读者尝尝鲜,我们很好奇这其中的含义,您能为我们解释一下吗?
刘心武:我种的四棵树,第一棵是小说树;第二棵是散文随笔树,我写的散文随笔出了很多集子,在《刘心武文粹》收录了好几本,有一些还比较流行,比如有篇《心里难过》,从网络上可以找好几种音频你,由不同的人士朗读,反响比较强烈,再如写我自己家族的,写我接触到文化名人的,都很值得一读。
另外我搞建筑评论,在《刘心武文粹》的最后一卷《刘心武建筑评论大观》中大家可以看到,也得到了建筑界一些老权威的认可。我评论的是公众共享建筑,和对建筑美学的探讨。比如探讨世界各大城市的步行街,在步行街上人的感觉,街道的宽窄和店铺的配置,以及它如何唤起人的内心的欲望,这些之间怎么协调。还有城市夜光的利用。现在很多城市乱亮,大量利用冷光,蓝光和绿光,但是不知道为什么这样用,没有美学依据,也不讲求冷光、暖光怎么搭配。
比如巴黎在城市夜光的使用上非常的讲究,基本上强调两个,冷光突出美感,白光打在古典风的建筑上,一目了然。另外用暖光点缀——店铺的商标和名称,用猩红色的红灯来燃亮。除了这些,在我的建筑评论里面,也涉及到普通老百姓的生活。比如谈室内望点,就是家里装修的时候有没有设计望点,是室内居住空间里最长视线的目光点。
记者:很多朋友对您的绘画功底也有所耳闻,会在这部《刘心武文粹》中有所展示吗?
刘心武:我的绘画多数是水彩画,个别的是综合材料画和油性笔画。水彩写生画完成的那个阶段是我生命当中很宝贵的一个时段,看我的水彩画可以理解到我内心的一些隐秘,和《刘心武文粹》的文字中的互相锲合。
记者:我注意到《刘心武文粹》的封面是您的个人肖像,据说是电脑油画,很有质感,也十分亲切。
刘心武:现在虽然新型的电脑上的绘画很流行,特别是在网络小说和动漫中的使用。这本书特别选用了电脑油画作为封面。这幅画并不是架上画,用传统的画笔和油画颜料在画布上画出来,再翻拍的效果,而是在不依靠传统的油画制作的工具,完全在电脑上完成的。
在此之前没有听说过这样来使用肖像画的作家,这也体现了我的个人风格。我在多种审美区域里选择了以写实作为创作核心,但是并不排斥其他的写法。我在《人民文学》杂志担任主编时容纳各种各样新的文学、文本方略、品类手法。所以这种做派也延续到《刘心武文粹》的编辑出版过程中,容纳度很大,也希望大家喜欢这套书。
记者:这种绘画方式叫CG,就是电脑绘画。封面画家和平先生在国际CG界也是享有盛誉的。
刘心武:我很感谢他在电脑上完成这幅画,而且他同意使用在我们这套书的封面上。另外凤凰壹力还出版了《刘心武文粹》的定制版,封面使用了皮革和我的自画像。自画像没有脸庞的轮廓线,突出我的大鼻子和我的小眼睛,抓住了我的相貌的几个特点,又留给读者一些想象的空间。
记者:其实文坛很多年纪稍长的作家到后期作品产量就会下降,您也说自己是一个马拉松型的作家,那您一直在长跑的秘诀是什么?
刘心武:我觉得秘诀就是坚持。我早期的时候退稿也特别多,那个时候的编辑部不像现在,不采用你的稿子只是留着不发,别人也不会知道。他们总是要把你的稿子退回来,同学嘲笑我,家里大人也烦。但是他们经常不手写退稿信,都是油印的,把稿子名字填进去,说感谢您给我们来稿,但是不合用,先退还给您,希望您继续支持。
时间久了,当初一起投稿的很多人,后来就打退堂鼓了,只有我坚持。帝王将相,宁有种乎?别人的东西能登出来,我的凭什么不能。所以我觉得坚持,不怕失败,不怕挫折是很重要的。我的第一篇稿子投给《读书》杂志,是一个学术性的高端文化杂志,稿子评论的是苏联的拉夫列尼约夫的小说《第四十一》,一般的学生读不懂,更不用说去评论。稿子登了以后,他们以为我是一个学究,或者起码是在大学教外国文学(苏联文学)的,就用墨笔在很高级的宣纸上给我写亲笔信,希望我多多赐稿。后来他们一调查,发现我高中没毕业,还是未成年人,让人失笑,就把后来的稿子退了。之后我就思考该如何继续投稿。
所以第一是坚持,第二个是调整,在坚持的过程中要不断调整自己的写作步伐。被退稿之后,家里大人说你还太小,起点就是拉夫列尼约夫,在苏联也是非主流的文化里一个很古怪的部分。
之后我就开始看一些报纸的副刊,写一些小的散文随笔诗歌,符合一个少年的状态。我喜欢写儿童诗和儿童题材的作品。后来的文章在《北京晚报》副刊发表的最多,还有《人民日报》、《中国青年报》、《光明日报》副刊等,逐步打开了局面。
第三就是一定要坚持自己的独创,要有绝活。我早期的作品都是顺应当时意识形态的主流的,但是在关键的时间节点上依然有独创的作品。1961年我写了一篇文章叫《水仙成灾之类》,这篇文章举某国为例,由于它的港口缺少花卉,就引进了风信子来装饰。但风信子极易繁殖,后来在水里长疯了,堵塞了海港,政府不得不花很多资金去消灭它。文章就是告诉大家,好事不能做过头,否则可能好事会变成坏事。
这篇文章很尖锐独特,并不迎合当时主流的观点。我把它寄给了《中国青年报》,刊登在1962年元旦那一期副刊的头条。30年以后,在1992年我已经成名了,我到温州楠溪江去旅游。那时候楠溪江有很多老作家、老艺术家和书法家去旅游,当时我在那里发现一个白发老头在江边老对我着笑,我就走过去对他点头。他说你是刘心武吧。我说我是。他说1977年我读《班主任》的时候发现署名刘心武,我就觉得这个人一定就是1962年发表《水仙成灾之类》的刘心武,在历史关键点能发出新的想法而且能被发表。原来他就是当时《中国青年报》的总编辑,我那篇文章就是他签发的。
我们两个聊了以后感慨万端。他说那时候你那么小,就能写出这样的文章。我说那个时候你居然能把它签发出来。旁边和他同行的人说,你可不知道,“文革”时期他为这篇文章受苦受大了,他就坚持说这是一个自发来稿。也确实是自发来稿,那一年我还不满二十岁。
这位老者当时是《中年青年报》的总编辑,叫孙轶青,孙老已经过世了,在报上看到他过世的消息我心里很难过,但能走到今天也说明我不断在遇到伯乐。
记者:像这样观点比较尖锐的文章,发表过程肯定是比较坎坷。
刘心武:《班主任》就很有争议,当时负责《人民文学》的是张光年,他召集编辑部开会,有的编辑说作品太尖锐,发出来会惹事。但也有人说它很真实,读者需要真实的作品。张光年说我发现你们两派争论当中有一点是共同的,就是觉得它写得真实。而现在是不怕尖锐,怕不真实,只要真实,越尖锐越好。所以《班主任》就发表了。发表之后很轰动,编辑部当时收到的读者来信每天有好几帆布口袋,多到需要发动所有编辑来参与拆阅。
以前《文艺报》的主编冯牧,也给了我很多扶持和关爱,没有他的支持我也不会走得这么顺利,所以有时候除了坚持、调整和原创之外,还得靠社会机遇和伯乐。
最近我写的一篇文章叫《诗画忆西行》,讲的是送给宗璞当作生日礼物的一幅画。宗璞在前几年搬家的时候不小心流失了,包括她个人的手稿,冯友兰老先生的书信,以及我的那幅画。但这幅画的照片还在,收录在《刘心武文粹》里。从这幅画的丢失到回忆起一些人,我个人受到这些人的扶持,永远也不会忘。
记者:我们刚刚告别了2015,迎来了2016年。在新的一年,对于喜欢和支持您的读者朋友有什么样的寄语和祝福吗?)
刘心武:在当代作家中我不是最受欢迎的作家,而且是有争议的作家,有些人不喜欢我的作品,我也很清楚在文学的流变当中,也在逐步被边缘化。
但是后来因为《红楼梦》的讲座,我又回到公众状态,所以读者读我的作品,读《刘心武文粹》,等于是我们之间的重新谈心。我希望你们喜欢我,但是不强求。
希望你们从我的书里面可以得到一些启示,如果你读过之后有所批评,对我更有警示作用。我们的人生在匆匆地消逝,我们都有很悲催的一面,最后都会死去,人生很短暂,所以一生当中能够和我们交朋友的书和作者也是不多的,真的不多。
人生中都有阶段性的爱憎。一个阶段我们喜欢一个作者,喜欢他的一些作品,过一阶段可能就不喜欢他。但既然有缘相遇,你遇到了我,遇到了书,翻一翻还是要珍惜。各自珍惜我们的各自独特的生命,比什么都要紧。我想这应该是能引起我们共鸣的一句话。
404 Not Found
- 《海洋文化十八讲》:叩开海洋探索新门扉
- 马伯庸:我最熟悉小人物的生活
- 博采旁搜 探微知著——读《苏轼诗文汇评》
- 一份珍贵的历史注解:评《中国互联网发展简史
- 李佩甫《生命册》:人性悖论的命运与时代变迁
- 《“大思政课”善用之》:寻找立德树人的答案
- 生活平淡 幸好还有文学
- 人工智能三部曲:从人文视角为青少年解读AI
- 让童书“好玩”又“好读”
- 第八届中国“网络文学+”大会将在京启幕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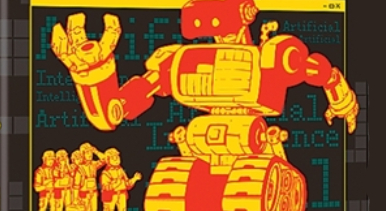













 京公网安备 11010102004843号
京公网安备 11010102004843号